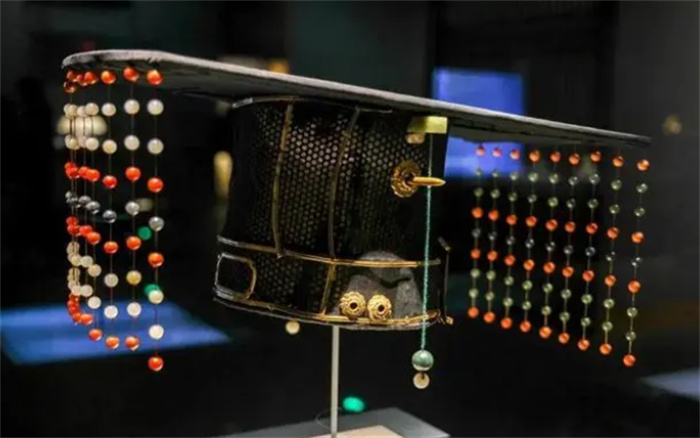周振鹤:论清末的废科举兴学堂的社会文化背景
清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四日,即公元1905年9月2日,清廷谕令立即停罢科举,废除了从隋代起绵延了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取士制度,该谕令后半段文字如下:
著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其以前之举、贡、生员分别量予出路,及其余各条,均著照所请办理。总之,学堂本古学校之制,其奖励出身亦与科举无异。历次定章,原以修身、读经为本;各门科学,又皆切于实用。是在官绅申明宗旨,闻风兴起,多建学堂,普及教育,国家既获树人之益,即地方亦有光荣。
科举取士制度是中国延续时间最长的最重要制度之一,而竟一旦予以罢废,对这样一件重大的历史事件,当时的社会上反应如何呢?相对冷淡。只有极少数的杂志对此事表示关心,而且这种关心只是停留在刊登袁世凯等人的奏折而已。报纸的反应稍积极,但也只有极少数的报纸,有简单的评论和报道。其中有些评论不但并不将立停科举当作如何重大的举措,且表示种种的疑问。这里仅以传播面最广的《申报》为例。在上谕下达的第四天,《申报》虽在第二版上作了全文刊载,但同时又以“谨注”的形式发表了一篇与今天评论员文章相似的文字。文中尽管承认科举制度的废除是一件大事,但是却又尖锐地指出:
今上谕谓学堂优予出身,本与科举无异,则日后毕业将至于中学生员、省学举人、大学进士,人人鹜此虚学趋于仕路,不几与科举之旧习名异而实同乎?
这句话代表了许多人的心声,正是这种科举与学堂无别的感觉,使得停罢科举的历史性举动没有引起多大的波澜。科举制度本是封建社会里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一种默契,在统治者一方是以此来笼络士绅阶层及一般百姓,以形式上平等的考试方法吸收部分士绅参政,使“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以维持社会的稳定;在被统治者一方则藉此而平步青云,换取功名利禄,进入统治者行列。这种默契的成立,使得科举制度尽管弊端丛生,仍能沿续千余年而不受改朝换代的影响。但是晚清以来,中国已无法继续保持锁国状态,西方新式的教育与考试制度明显优于科举制度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因此改革以至罢废科举成为清末改革的焦点问题之一,虽然在起初就是激进的维新人物也并未坚决主张罢废科举,但到后来即使重臣勋贵也都倾向于科举非罢废不可的建议。于是科举的废除变成只是时间问题,在欲废未废的这段时间里,在高层统治者与士绅之间都持一种观望态度,以寻求一种双方都能接受的新的默契。最终,由最高统治者以用学堂出身代替科举出身的办法昭告天下,而废除了科举制。因此废科举兴学堂是新的一轮默契的成立,这一默契与前一默契形式上改变而实质上不变,这对订立契约的双方来说都是心知肚明的。
下面先对清末罢废科举的全过程作一鸟瞰式的回顾,然后再回溯科举制产生的背景,以看出两种默契是如何转换的。
十年历程
清末科举的废除并非一时的行为,而是一个长时段的过程,如果从1895年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算起,可以说整整花了十年时间,才有这最后的结果。在此对最终的这个上谕,有两种感觉同时存在,一是早该废除了,一是废除不废除都一样。既然有这两种感觉,那就无怪乎引不起社会大的震荡了。
首先让我们以年代为经,将一系列的反对与改革科举的言论简介如下:
1894年中日甲午之战满清败于日本之后,人人皆有忧国之思,亡国之惧,因此只要有关改革旧制的建议都会引起普遍的响应。
1895年,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中有教民一节,列举科举之弊,主张三场考试的第二场试掌故策,三场试外国考,殿试则试策问,头场虽仍试四书文,但让试者“纵其才力,不限格法,听其引用(过去不准用秦汉以后书与诸子书)。”不过康氏并未提出废除科举制,这是十分初步的要求。
1896年,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论科举》,认为“欲兴学校、养人才以强中国,惟科举为第一义。”并提出变革的上策是“合科举于学校”,这实际上是主张废除科举,而以学校为取士之源;中策是“多设诸科,与今日帖括一科并行”,以免有实学之人才流失;下策是“乡会试必三场并重”,防止只重第一场的八股文。
1897年,徐勤在《时务报》警告说:“覆吾中国,亡吾中国者,必自愚民矣,必自举业愚民矣。”痛斥八股文之害,疾呼废除科举制。
但是如徐氏主张全盘废除科举制的人并不多,上述梁氏之言论表达了当时的社会思潮,欲以上策为理想,而愿从中下策开始变法。所以梁氏之三策以及其他人士的改革意见提出前后,清廷在不同程度上已作了政策上的调整。于梁氏上策而言,虽不能合科举于学校,但已于1896年筹备建立京师大学堂。于梁氏中策而言,则有1897年贵州学政严修奏请设经济专科之议,第二年初即准备经济特科与岁举两途并行。严修之议实质上是分科举之势,使部分人才能由经世致用的途径出。
至1898年四五月间,由于维新志士们的宣传效果,内外臣工上书请废止八股、改革科举制度者纷纷:
4月6日,浙江巡抚廖寿丰在严修建议的基础上进而主张经济岁科不应附庸乡、会试,亦不应试四书文,实际上是主张经济学堂的学生成绩优秀者可以有同进士出身的资格。
14日,御史杨深秀有奏请厘定文体一折,猛烈指责制艺贴括之消磨人才。但又因制艺之科行之已数百年,猝无善策更之,因此主张以取消八股文体作为改革科举制之先声。
6月17日,康有为上《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析》;
同日,御史宋伯鲁亦上《请改八股为策论折》(实为康有为代拟);
22日,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上《请废八股育人才折》(亦为康有为代撰);
这些奏折力陈八股之害,是自明代以来类似言论的继续,但是在当时有亡国之忧的背景下说来更加痛切。
在维新派不断地鼓动下,在全国之势的改革气氛中,光绪皇帝的反应也极其快速,先在杨深秀上奏后,当即谕示各项考试不得割裂经文命题。又于徐致靖上疏后的第二天,即6月23日,颁发了《自下科为始,乡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向用四书文者,一律改试策论》的上谕。这可以算是改革科举制度的第一步,也是自明代成化年间实行八股取士以来第二道废止八股文的谕旨,其文略曰:
我朝沿宋朝旧制,以四书文取士。……及近来风尚日漓,文体日敝,试场献艺,大都循题敷衍,于经义罕有发明,而谫陋空疏者,每获滥竽充选若不因时通变,何以励实学而拔真才?著自下科为始,乡、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向用四书文者,一律改试策论。
尽管在康熙初年也曾有过废除八股文的成例,上述谕旨还算不得是什么惊人之举,但为了坚定光绪皇帝的变法信心,一周后(30日)康有为还代宋伯鲁拟了一份《请废八股勿为所摇》片。而且究其实光绪这一步迈得并不算大,因为当年本科本试刚结束,去年乡试也刚过,若自下科为始,最快要等两年以后才有实际的改革行动。维新派等不得这种蜗行牛步,同日又由宋伯鲁出面提出一份奏折,请将经济科归并正科,各省岁科童试立即改试策论。光绪立即发上谕表示同意,其速度之快,即在今日亦洵称奇。
又过十天,即7月10日,掌管科举事务的礼部尚书怀塔布,将该部依据光绪两次谕旨讨论拟定的具体改革条款上奏(见《戊戌变法档案史料》)。同时又询问向来头场考中的必有的五言八韵诗是否仍旧命题?不久,光绪即明示,“嗣后一切考试均著毋庸五言八韵诗。”
看到光绪表态于上,封疆大吏也纷纷响应于下。
7月4日,湖广总督张之洞、湖南巡抚陈宝箴联名具奏《妥议科举新章》,倡言“求才必自变科举始”,不但对废止八股文极表赞同,且提出“先博后约,随场去取”之法。此法是将原三场考试次序颠倒,第一场试中学经济(即中国传统学问中的经国济民之学),取预定录取人数的十倍,取中者方准试二场;第二场试西学经济,取预定录取人数的三倍,取中者进入三场;第三场才试四书义与五经义,合格者就是最终录取者。据说在夏历闰三月间,张之洞已与鄂、湘抚会商请改科举之法,后见光绪下诏废止八股,立即上此长奏。19日(《清德宗实录》系于七月初三,即8月19日,不知孰是),光绪同意此奏,并赞其“所奏各节,剀切周详,颇中肯綮。”22日,又谕礼部详议条目颁行。同时又谕示:“嗣后一经殿试,即可量为授职,至于朝考一场,著即行停止。……不凭楷法取士。”
7月15日,湖北巡抚谭继洵(谭嗣同之父)继张之洞、陈宝箴之后亦上一折,中有“筹科举即出于学校”一策,是将前述廖寿丰所建议的,迳由学堂先举的经济岁举扩大岁科与乡会试正科,使科举虽存而犹亡,因为所有人才如果都从学堂出身,则科举将无人钻营。
8月27日,光绪又下谕批准徐致祥之奏折。徐折专就岁科生童两试而言,指出经古一场考试如不改革,则策论之试不专。主张岁科两试清照乡会试新章,分场去取。使从来之八股文体即在生童考试阶段亦无容身之地。
重要的改革科举条陈及举动大致如上所述,从中可以看出即使重要维新人物亦少有废科举于一旦主张,而是将停止以八股取士作为改革的重点,同时化科举单一的取士之道为多元地提拔人才的途径。而光绪所同意的改革方案亦皆不出此二方面。但即使是这样比较温和的倡议,也受到多方的阻格。据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所说,康有为与杨深秀于夏历三月时曾上书,为礼部尚书许应骙所驳。四月初旬,梁启超复联合举人百余人,连署上书,亦格不得达。故五月初而有宋伯鲁攻击许应骙守旧迂谬、阻挠新政之奏,两天后许即予以回击,而光绪此时尚取息事宁人态度,未即解除许氏之职,只是下诏表明废止八股文的决心而已,而上面已说过这一步其实迈得并不大。而且所有主张温和地改革的建言亦多未曾付诸实施,便遭遇了戊戌政变。政变发生在9月21日,首先当然先解决军政大权问题,至第十九天,即10月9日,便有太后懿旨,对基本上尚未着手进行的科举改革开刀:
国家以四书文取士,原本先儒传注,阐发圣贤精义。二百年来,得人为盛。近来文风日陋,各省士子,往往剿袭雷同,毫无根柢。此非时文之弊,乃典试诸臣不能厘正文体之弊。……用特明白宣示:嗣后乡试会试及岁考科考等,悉照旧制,仍以四书文试贴经文策问等项,分别考试。经济特科,易滋流弊,并著即行停罢。
科举改革如同其他戊戌新政一样,不过昙花一现,而且比其他新政更多地只体现在纸面上而已。真正大声疾呼要将科举一举而摧毁之的主张出现在庚子事变以后,清政府被迫实行新政时期。
这一时期也可以以年代为脉络来看出究竟。
1900年,义和团起于山东,八国联军入京师。清廷逃往西安。
1901年1月29日,清廷在西安下诏变法,要求内外臣工在两个月内“详悉议以闻。”这是再次挨打重创以后无可奈何的补救。于是变通科举再次成为热门话题。
4月,山东巡抚袁世凯上奏,建议逐年核减岁科乡试的取中名额,另增实学一科。将旧科所减之额,作为实科之数减到五成为止,此时学堂中多成材之士,考官中亦多实学之人,然后将旧科中五成中额,一并按照实科取士章程办理。(《经世文新编续集》卷一通论中)
7月12日,两江总督刘坤一与湖广总督张之洞会衔上疏,认为:酌改文科科举一事,为自强求才之首务。……拟即照光绪二十四年臣之洞所奏变通科举,奉旨允准之案酌办。……是故渐改科举之章程,以待学堂之成就。……俟学堂人才渐多,即按科递减科举取士之额,为学堂取士之额。
此两折实际即釜底抽薪,使科举名存而实亡,但名义上仍保持科举制之存在。但两广总督陶模的奏折则直以废除科举为说,痛陈:“自甲午以后,诏设学堂者屡矣,而人才不出,何也?则以利禄之途仍在科目,欲其舍诗赋、八股、小楷之惯技,弃举人、进士之荣途,而孜孜致力于此,此必不可得之数也。是故变法必自设学堂始,设学堂必自废科目始。今宜明降谕旨,立罢制艺、大卷、白折等考试。……科目既废,进身之阶舍此末由,自无不踊跃从事(按:指入新式学堂)。(同上揭书)
陶模此论之直率剧烈连维新之士亦未尝多见。当然清廷不可能一举废去科举制度,而是选择能够表明改革决心而又影响不大的举措来应付。首先是在6月3日,有举行经济特科之诏,接下来才有8月28日自打耳光的科举罢时文试帖,改以经义时务策问试士的上谕。这就是说在兜了一圈,五年之后,又回到原来的停试八股文的老地方。而且此诏书不但在内容上与五年前的那份相同,甚至连行文口气都无大差:
我朝沿用前明旧制,以八股文取士,……乃行之二百余年,流弊 日深,士子但视为弋取科名之具,剿袭庸滥,于经史大义,无所发明,急宜讲求实学,挽回积习。……着自明年为始,嗣后乡会试,头场试中国政治、史事论五篇,二场试各国政治、艺学策五道,三场试四书义二篇、五经义一篇。考官评卷,合校三场,以定去取,不得全重一场。……以上一切考试,凡四书、五经义均不准用八股文程式,策论均应切实敷陈,不得仍空衍剽窃。
但此次科举之改革亦只到此为止,清廷对刘、张之奏与陶模之折还无任何表态。直到10月2日才空头地对前者表态说:“刘坤一、张之洞会奏整顿中法,仿行西法各条,事多可行,即当按照所陈,随时设法,择要举办。”但只字不及科举改革之事。可见保守势力视科举为重要堡垒,不肯轻易退却。11月12日政务处会同礼部议复刘、张之奏,并不采其“分场发榜,各自弃取”之议,反以为“乡会试分场弃取,不免有偏重之弊,目前仍宜三场合校,毋庸更张。堵死了进一步改革之路,更不用说全盘废止科举制了。
一年多以后的1903年初,下诏为庆祝明年慈禧七十寿辰而筹备癸卯恩科乡试与甲辰恩科会试,丝毫没有废除科举的意思。
但是洞悉中国弊病的有识之士与部分高级官员明白科举制度存废关系国家的兴亡,因此第三度提起改革科举的话题。1903年3月13日署两江总督张之洞又会同直隶总督袁世凯奏请变通科举,明确指出科举不废,则人人有侥幸观望之心,无人肯上新式学校学习,故各省于兴立学校一事,大率非观望迁延,即敷衍塞责:
其患之深切著明,足以为学校之敝而阻碍之者,实莫甚于科举。……何者?利禄之途,众所争趋;繁重之业,人所畏阻。学校之程期有定,必累年而后成材;科举之诡弊相仍,可侥幸而期获售。虽废去八股试贴,改试策论经义,然文字终凭一日之长,空言究非实谊可比。……人见其得之易也,群相率为剽窃抄袭之学,而不肯身入学堂,备历艰苦。善谓入学堂亦不过为得科举地耳,今不入学堂而能得科举,……又孰肯舍近而图远,避易而就难?
但对于实际操作,张、袁亦并不提议立即废科举一旦,而仍重提按年递减科举考试取中之额,并将所减之额移作学堂中当取之额的办法。但是此折递进后交政务处议奏,却没有下文。
于是在1904年1月13日,张之洞与张百熙、荣庆在联衔奏《重订学堂章程折》时,又附片请“递减科举、注重学堂”,强调“时局阽危,非人莫济,除兴学堂外,更无养材济时之术。”主张自下届丙午科(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起每科分减中额三分之一,俟三科后中额减尽,即停止乡试;岁科试中额亦相应减少,俟学额减尽,即行停止岁科试。以后生员即可尽出于学堂。此奏的最终目的是要废除科举,但所采用的是渐进的,将科举制消弭于无形的办法。这个提案总算邀准,但在年底何时废除科举这一点上清廷仍含糊其词,谕令说:“著自丙午科为始,将乡、会试中额及各省学额按照所陈,逐科递减。俟各省学堂一律办齐,确有成效,再将科举学额分别停止,以后均归学堂考取,届时候旨遵行。
可见清廷还是没有废除科举制的打算。因而在一年多以后,更剧烈的要求由袁世凯等人提了出来。1905年9月2日,直隶总督袁世凯会同盛京将军赵尔巽、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周馥、两广总督岑春煊与湖南巡抚端方上折,请立停科举,以广学堂。认为“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以分其砥砺之志。民间更相率观望,私立学堂者绝少,非公家财力所能普及,学堂决无大兴之望。就目前而论,纵使科举立停,学堂遍设,亦必须十数年后,人才始盛,如再迟至十年甫停科举,学堂有迁延之势,人才非急切可求,又必须二十余年后,始得多士之用。”因此科举非即时停罢不可(据陈恭禄《中国近代史》584页录有袁世凯之奏语曰:“科举一日不废,即学校一日不能大兴,学校一日不能大兴,即士子永无实在之学问,则国家永远无救时之人才,中国永远不能进于富强,即永远不能争衡于各国。”不知此语从何而得,谨附于此以作参考)。
袁氏等人奏折所举理由虽以科举“阻碍学堂,妨碍人才”,但这一点其实并不对清廷的统治构成威胁,威胁是来自“现在危迫情形,更甚囊日”。就在上文张之洞之奏折与此次袁世凯奏折之间,已发生了世界史上的一件重要大事——日俄战争。战争虽是为解决日本与俄国之间的矛盾,但战场却在中国,所争者为两国在华权益,而清廷竟宣布中立,这不但是大丢脸面的事,而且也是明显的亡国之兆。袁世凯等人都是封疆大吏,五年前南方之总督巡抚们已有东南互保的半独立行为,若清廷再不接受这次的提案,则这些方面大员的向背将直接影响清廷的统治,尤其上折者一为直隶总督,直隶是统治核心区;一为盛京将军,盛京乃是满清老窝;南方最重要的三大总督亦皆列名其中,万一再有其他变故,则亡国可立待。
因此真正使科举得以废除的并不是这些大臣的各种奏折,而是“时局阽危”、“现在危迫情形,更甚囊日”的威慑作用。除了日俄战争的冲击以外,立宪的呼声已经到处可闻,革命团体华兴会、光复会与同盟会相继成立,革命已是近在眉睫之事,专制制度面临即使不覆亡也有被严重削弱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清廷不得不在一些非致命性的问题上作出让步,于是而有在1905年9月2日下诏立停科举之事。
一个人人皆知其为弊病丛生的制度,其废除过程竟延续了十年之久,除了保守派的负隅阻挠外,必须还有更为深刻的社会原因在。
千年默契
这个社会原因就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默契。统治者以利禄来劝诱少数被统治者参与统治,作为稳定国家的最基本的措施之一,亦即所谓“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而被统治者则为一己的私利,而埋头于熟读经义之中,以冀有朝一日能登天子堂。从隋代实行科举制以来,直到清末罢废以前的千余年间,尽管有种种批评科举制弊病的议论与不断变化的考试,但这一默契始终不变。
科举制度与许多其他后来变成历史前进绊脚石的制度一样,在实行之初是有其进步意义的。其进步性就体现在比此前的任何举官制度都要平等。回溯历史,在春秋时期以前,实行的世卿世禄制。这一制度简而言之,就是以血统作为当官的唯一标准。只有贵族才具有当官的候补资格。春秋战国之际社会大动荡大分化,世卿世禄制度受到挑战,出身虽不高贵,但有才有学的人逐渐有了食禄当官的可能。所以孔子办私学,以“学也,禄在其中”作为广告,吸引人们向学求官。孔子本人也到处兜售自己,担任了短时间的鲁国司寇。把学与禄挂起钩来的政策在数百年后的两汉时期得到了发展,《汉书·儒林传赞》对此有所描述:“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派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有才学且品行端正的人在两汉时通过察举制,即乡举里选制,被逐级推举到政府里当官。被推举到中央的人带要接受皇帝的策问,以觇其实际上的行政能力。如西汉的第一布衣宰相公孙弘,头一次策问就未通过,到六十余岁才在第二次选举中被武帝所赏识。但这种举荐制度有明显的缺陷,那就是容易产生弄虚作假的弊端。所以东汉时便有“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之叹。为纠正这一弊病,魏晋南北朝采用九品中正制,在州郡两级分别有小中正与大中正两级官员,专门鉴定人物的品级高低,以备录用。尽管如此,能列为上品的仍是贵族,而出身寒微者只有名列下品的份。
于是从隋代起,九品中正制遂被科举制所取代。从形式上看来,这是一个在考试面前人人平等时代的开始。这一制度使人的品级从以出身为准,真正转变为以才能为准,而才能的标准则是考试的成绩。所以这时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相对于九品中正制而言显然是进步的。由于是凭考试当官,就使得“朝为读书郎,暮登天子堂”成为现实而不是梦想,相对而言使国家能得到有真才实学的人来参与治理。但是利之所在弊亦随之,这就是科举制度与生俱来的两个无法克服的毛病。
第一个毛病是目的不正。这个毛病又可从两方面来看,一是参加科举之人非为造福社会,而是为一己当官食禄的私利;二是主持科举的统治者,是要以笼络人才来为自己的统治服务。统治者视科举为愚民之术,绝不肯轻易放弃。从隋唐以来科举就有笼络天下英俊的企图,到明清以后则更有消磨海内志士意志的目的,使千百万人埋头于时文贴括之中而不能自拔,明显对于稳定统治有莫大的好处。由于科举制度能满足双方的需要,实际上就成为双方之间的一项默契。不但统治者要维持科举制度,使之长存不废,在被统治者一方更未想到这个制度会有结束的一天。因此科举制的这第一个毛病反而成为使这个制度得以延续千年的原因。与此同时,这个毛病基本上是不可克服的。因为在农业社会里,读书做官是最佳的前途,所谓“学得千般艺,货与帝王家”,说的就是这一社会现象与心理状态。对于这一现象,许多有识之士很早就表示过不满。尤其是南宋的理学家朱熹多次批评科举制度,他说:“可惜举业坏了多少人”,尖锐地指出其目的的不高尚。目的既不高尚,也就不能得到真正的人才。这一观点直到清代还有人屡屡言之,如清代乾隆初,兵部侍郎舒赫德就认为“人才之盛衰,由于心术的邪正”,而科举制度导人以侥幸求售之心,弊端百出,于人之道德气节,转足为害,因此主张朝廷“别思所以遴拔真才实学之道”。但是大部分人虽然觉得科举制度不理想,却想不出有更合适的办法来取代它。即使朱熹也不得不承认这一制度不易改革,叹息道:“居今之世,使孔子复生,也不免应举。”
而且由于目的不正而使得学校变成不是育才之地,而是准备应试的储才之所。更由于中式与落第者(或未及第前)的地位名誉与利益的巨大反差,而使人不但不去顾及目的高尚与否,而且不认为科举应该改革,而只是拼命只想通过科举去改变自己的地位,因为一旦改革则自己反而失去了安身立命之处。据《郎潜纪闻》纪载:“翁文端公(翁心存,即翁同和之父)年二十四时,犹一贫诸生也,其祀灶诗有云‘微禄但能邀主簿,浊醪何惜请比邻。’士当困厄无聊,易作短气语。当公为此诗云,岂自料两朝宰相,再世帝师,三子公卿,四世翰苑,功名福泽,为本朝希有人物哉。”翁心存在未中式前只敢企望微禄,不料平步青云,天下闻名,这种反差何等憾人,无怪乎人皆用心于科举而不思其弊病所在。
科举制的第二个毛病是考试方法有问题。因为有才能的人不是用简单的手段可以考出来的。既然形式上公平的科举制度难于取消,那么改进的办法只在于改善具体的考试方法。这就是如何减轻第二个毛病。唐代是诗赋取士,诗赋不但标准难定,而且于治国无关。宋代王安石变法,计划建学校、变贡举、罢诗赋,以经艺(即理论与实际办事能力)取士,然因变法失败而未果。欧阳修知谏院时,也提议以策论代替诗赋,并改为三场分试,每场有淘汰。头场策论合格者试二场,二场论合格试三场。南宋朱熹则提议兼试其他科目,以使应试者有真本事。到了明朝,则科举之法改而为以经义取士。为了防止作弊,容易批阅,第一场所考经义且有一定的作文范式,俗称八股文。因以四书为说,代圣贤立言,又称四书文,又称时文。既有一定格式,就不能发挥自由思想,就会产生模仿剿袭,有真才实学的人有时不得不受其所累,而禁锢了自己的聪明才智。
以八股文取士,人人都认为应予废除,而且也一度有废除的记录:康熙二年下诏曰:“八股文章,实与政事无涉,自今之后,将浮饰八股文章永行停止,惟于为国为民之策论中出题考试。”但停止却只一时,并未“永行”,两科以后,恢复旧制。虽然以后仍不时有反对八股之议论出现,但都不成气候。真正成为规模性的改革科举制度(包括主张一举予以废除或实行某种程度上的改革)的运动,直到戊戌变法前夕才出现。
新默契的成立及其遗害
虽然戊戌维新前夕已形成规模性的改革科举的运动,并且在百日维新中将废止八股的主张付诸实施,但连这点最起码的改革,也夭折于摇篮之中,遑论罢废整个科举制的主张了。科举制度改革之难还不单是一个制度的问题,而是改变一种社会习俗,矫正一种社会心理的问题。在通常所说的文化三层面中,制度是中间的一个层面。虽然比物质文化难以变革,但相对于精神层面而言,还是较易于动摇的。问题在于一项制度行之已有千余年,无论是利用这一制度的统治者一方,还是受此制度制约的被统治者一方,都产生了一种心理上被束缚的感觉。纵使这项制度百孔千疮,双方所想的也只是补罅苴漏,而不是去旧图新。因此科举制度的改革实质上仅是制度上的更新,而且还有移易风俗、改造心理的成分在内。只要随便几个例子就可说明科举制度如何影响了或者说如何规范了民风与士习。
明朝著名学者艾南英《应试文自叙》云其“为诸生者二十年,试于乡闱者七年,饩于二十人中者十有四年”,于各家制义无所不习,而未中式。“第一念至,欲弃举业不事,杜门著书,考古今治乱以自见于世,而又念不能为逸民以终老。”艾南英屡试不售,灰心已极,但还是继续考下去,虽不想当官,但也不甘心于连一个小小功名也弄不到,那到底太丢人了。如果说这在明代还不可笑,那么到清末,连严复这样洋派人物也以不得功名为耻,回国后仍要去参加科举,似乎就有点让人笑中含泪了。而且社会风气一旦养成,即使个人想要摆脱世俗之累,也是难乎其难。清初顾炎武说“余少时见有一二好学者,欲通旁经而涉古书,则父师交相谯呵,以为必不得专业于帖括,而终将为坎轲不利之人。”
清末反映社会风俗画面的《点石斋画报》,就有不少与科举有关的社会生活图。以辛卯年出版的石集为例,在形形色色的107幅图中,就有7幅是直接讲到科举的,分量不小。这七幅的标题依次为:南闱放榜、西人赴试、预迎经魁、侥幸成名、望榜笑谈、抡元佳话、及第先声等。以南闱放榜为例,该图描绘的是江南考区乡试放榜的盛况,中举者有正榜145人,副榜21人。在小小的画面上,新科举人的名字籍贯竟都历历可辨,因为登榜者不但有关利禄且影响到脸面,故而连一小幅风俗画也不敢马虎。屡试不售是很难堪的事,而一旦金榜题名,又极为光荣。湘军著名将领罗泽南七应童子试,不售,及入县学,泫然泣下曰:“吾大父及母勤苦资读,期望有年,今不及见之稍慰也,痛哉!”他当时还只是考中秀才而已,就如此感慨万千,中举当然更是天大的事。预迎经魁则是湖北特有的习俗。在每届秋闱放榜前,湖北省城都有迎五经魁的游行,这个游行的末尾竟然是江夏县右堂!由于科举制已融入社会习俗之中,而且科举制又与士绅阶层,甚至一般农民的利益相关,彻底改变殊非易事,这就使得官绅之间要有一段互相观望的时间。因此尽管在时局阽危的情况下,清廷已有罢废科举的趋向,但仍不敢贸然从事,表面上仍然按兵不动。
也因此,从局外人看来,立停科举的上谕是因袁世凯等人的奏折而下达的,其实在公开的立停科举的奏折和上谕背后有着一番高层统治者之间的磋商,《时报》当时对此有过连续报道,但不为今天的研究者所注意。据报道,立停科举事首先是端方在慈禧太后召对时所提出,得到初步同意,并受命与当时几位最重要的封疆大吏,即南北洋大臣、两广总督、两湖总督与奉天将军商议,这些人都表示支持,而后才由袁世凯撰写奏折,再经张之洞略改数处,而后于9月2日呈递,于是当日就发布上谕。这些幕后活动虽然是新闻界的报道,但可信度很高,在重大举措之前,高层统治者之间不可能不先统一步调。问题是,除了方面大员的支持外,清廷的最高统治者的决心是如何下的。报道又说,慈禧太后(报道虽均以“两宫”这说,其实谁也明白光绪皇帝不过一个傀儡而已)当面问过端方,如果废了科举,学校是否真能兴起。这个话的实质是问,学校是否能代替科举。端方明确回答,只要给予奖励,必能使富绅勇于兴学。这个回答骨子里是要求学校出身要与科举相当。所以才有立停上谕的那句话:“学堂本古学校之制,其奖励出身亦与科举无异。”这句话使得废科举有了最广泛的社会基础,消除了士绅阶层的疑虑,成为官绅之间新的一种默契。
事实上还在1901年7月张之洞、刘坤一会奏递减速科举取额后不久,即9月14日(光绪二十七七年八月初二),清廷已要求各省及学部筹议学堂出身章程,惟直隶总督袁世凯首先将前在山东任内之办法奏复,政务处及礼部即据以厘订章程,摺上于该年十月,以科名奖励学堂毕业生之声。
新默契的成立使办学的成绩突然提高:废除科举前的1904年,全国学堂总数为4,222所,学生总数为92,169人;五年以后的1909年,这两项数字分别变为52,348所与1,560,270人(第三次教育统计图表,宣统五年)。很显然,新式学堂成了科举的替身,这是明眼人谁也看得出来的。只有某些洋人似乎比较天真,将立停科举的上谕看成是“中国振兴之新纪元”的标志。《万国公报》九月号“时局”专栏以中国振兴之新纪元为题全文刊登了停罢科举的上谕和袁世凯等人的长折。并在此前加了按语:“中国政府近于改变之事颇有可观而立废科举一节取数十年来败坏中国及近日屡蹶屡起、根深柢固之附属物一旦拔弃之,是真中国历史上之新纪元而东方大局之转移在此矣。本馆记者不禁为之额手,爰取此次谕折冠于‘时局’之首,以明其关系之大,固不仅在中国也。”林乐知一类人到底太不了解中国了。
虽然立停科举的上谕在官绅之间建立了新的默契,但并非所有的人马上予以认同。在上者有人不同意:据新闻报道,某大军机就不以立停科举为然,要求按照新规定,将袁氏奏折交部院各署会议,各抒己见,再行酌核。某尚书担心部院多守旧之士,若交会议,徒乱是非,致阻新机,故未交议即请降谕。在下者也有人不买帐:在毁学校者,有集会抗议者。如四川广安州学校一毁再毁,如江西秀才千数百人集会,公举代表要求将本省举贡生员选入学堂肄业,否则将不交纳课税等等事件。但这些事件都不成气候,废科举兴学堂的转换过程没有产生太大的波折。因为大多数人心里明白,学校不过是“科举之变相”而已,名异而实同,因此就既无激烈的反对者,也无热情的支持者。其实何止科举制度如此,许多不合时宜的典章制度早应改革,但不到不得已的时候,改革反被视为不合时宜,但到不得已时,这一改革往往已失去时效,只有用革命来快刀斩乱麻了。
学校与科举原有根本的差别,前者重在育材,后者重在用材。学生所追求的是学问,生员所考虑的是利禄。由于科举制不是废于一旦,而是迁延十年之久,最终又以一种貌废而实存的形式延续下去,这就使得名为学校而实同科举的教育制度越过辛亥革命而遗害民国,“读书做官论”始终没有失去它的魅力,连革命也无奈何于由考试而弋取利禄的这团乱麻。孙中山先生的五权分立表面上是西方资产阶级国家三权分立的发展,实际上还是不脱中国旧制。考试本不应使之权力化,否则考试院不过是清代礼部与吏部两者的合一而已。
改革科举制度的运动从1896年算起已经过去一百年,但是整个科举制度的废除过程还值得我们反思。
来源:《复旦学报:社科版》1998年第4期
北京警方逮着一公交上行窃小偷,交代才知是窃走国宝大盗
小偷竟然是文物大盗本文作者倪方六上一篇“梧桐树下戏凤凰”头条号中,说了河南山里一户人家秘藏皇帝御赐镇宅“鬼画”被盗的事情。怪的是,这画没有几人知道藏在哪,怎么就不翼而飞了呢?“鬼画”是皇帝御赐的《钟馗捉鬼图》,知道家里的镇宅之宝不见后,这户宛姓人家赶紧去派出所报案。立案后查了很多村邻、族人,始终没有发现破绽。我要新鲜事2023-05-26 22:37:510000最难盗墓的墓穴 有着5000多件陪葬品(亲王墓穴)
明仁宗的第九个儿子墓葬当中有5000多个陪葬品。在我国古代的很多墓穴中,但凡是比较豪华的,一般来说都是和皇帝有关的人,不过从古代到现在,皇帝一共也没有那么多,但是皇帝的兄弟们还是挺多的,这些人一般都可以被称之为亲王,虽然和皇帝还是区别很大,但是他们的社会地位也是非常的高,在前几年我国也出现了一些亲王的墓穴,其中有一个比较难盗的墓穴。湖北发现我要新鲜事2023-05-01 13:11:020001美国工人修路时,意外掘出古墓,却发现:墓中所葬不是人类
《前汉书》记载:“方今之世,奢侈罔极,靡有厌足。车服、嫁娶、葬埋过制,吏民慕效,寝以成俗。”自秦始皇开启厚葬之风以来,影响力一直延续到两汉。无论是婚嫁还是葬埋,官吏民众都追求奢侈,逐渐形成一种风俗。我要新鲜事2023-05-27 19:59:220001考古新发现,“周道”是成周宗周往来干道、王公贵族家国情怀纽带
我要新鲜事2023-10-02 18:13:310000中国有个县盗墓者最爱去,地下文物丰富,县博物馆藏国宝160多件
盗墓者最爱去的地方本文作者倪方六如果问盗墓者最爱去什么地方?当然是地下有墓的地方。那么哪些地方有墓?这里面就有内容了。可以说,在中国,只要有人住的地方,地下都有墓,但墓与墓不同,老百姓的墓能有什么随葬品?白花吃奶的力气去挖。我要新鲜事2023-05-26 17:46:01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