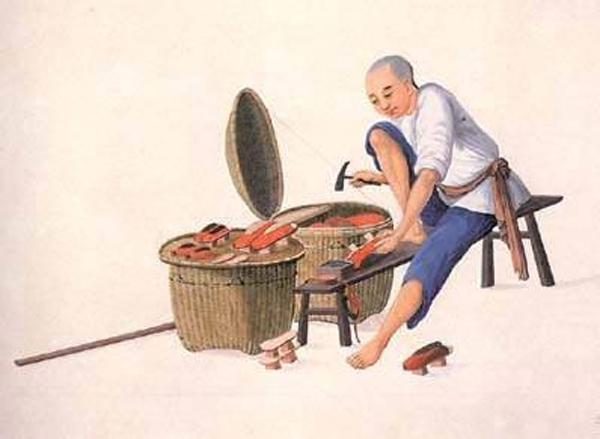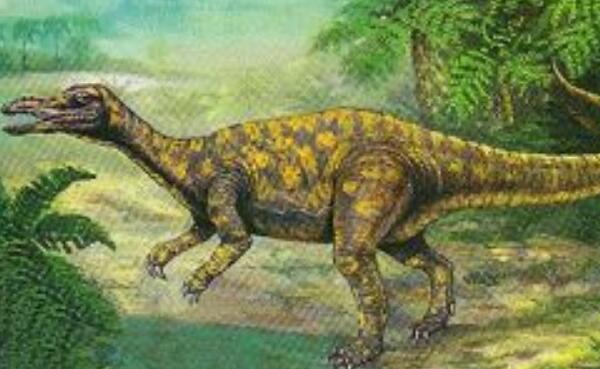土中找土 知多惑多——如何认识陶寺宫城大型建筑基址?
张小筑
6月3日,“2021年陶寺宫城大型建筑基址考古现场会”在山西襄汾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国家博物馆、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等高校和考古文博单位的40余位学者参会。
 讨论会现场
讨论会现场
 讨论会现场
讨论会现场
 参观遗址
参观遗址
在聚落考古、城址考古、建筑考古等发掘与研究方面经验丰富的专家学者参观发掘现场后,提出了重要见解和宝贵意见,为陶寺宫城大型建筑基址把脉会诊。
此次会议分为遗址考察、项目汇报和专家座谈三个部分。6月3日上午,与会学者前往陶寺遗址发掘现场进行参观;3日下午的讨论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研究室主任徐良高研究员主持。襄汾县委书记乔飞鸿在致辞中对专家学者的莅临表示欢迎与感谢,并指出陶寺遗址考古工作为考证襄汾历史提供了重要支撑、对探索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和尧舜时代的社会历史具有重要意义。随后,社科院考古所高江涛研究员从发掘缘起与简要回顾、发现与收获、意义与存在问题、下一步工作计划四方面对陶寺宫城大型建筑基址进行汇报。
据介绍,此次发掘从2018年3月开始,截至目前发掘总面积5041平方米,取得重要收获。发掘初步弄清了宫城内最大的宫殿建筑IFJT3的规模、四至、堆积、年代、布局结构,并对性质有了简单的理解。
 参观遗址
参观遗址
这个大型建筑基址究竟是怎么样的?
目前对它有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发掘进一步确认了宫城内面积近8000平方米的最大宫殿建筑IFJT3的存在,是迄今史前时期最大的夯土建筑基址。
第二,该建筑基址之上发现有2座主殿、东侧附属建筑、中部庭院、东部疑似廊庑、南部门址等等,其结构复杂、布局规整,史前罕见。
第三,该建筑基址延续使用时间长,显示出特殊的功用,或为“殿堂”一类建筑。
第四,建筑基址之上的主殿D1是目前考古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最大的单体夯土建筑。
总之,陶寺遗址宫城内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发掘与发现,对于中华文明起源问题以及早期中国等重大课题研究具有推动意义。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赵辉教授指出,陶寺考古工作意义重大。在中华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上,大格局已基本形成共识。目前的研究可能遇到瓶颈,进一步的突破点在何处?静下心来,要把重点放到区域性中心聚落并做长期工作,把最关键部分揭示清楚,这可能是复原和理解当时社会的关键。
赵辉强调,陶寺发掘难度极大,要把很多钻探材料落实,踏实地做陶寺。陶寺的发掘也从侧面反映出做大遗址难度之大。此外,陶寺宫城大型建筑基址位于重要宫城重要区域,犹如皇城台之于石峁,从现场考察来看,情况复杂,并非一个时期简单的平面结构。对于开展下一步工作,要关注大台基下面的遗迹现象和地层状况以及房址与大台基是否同期。
“发表的材料意见不必非常绝对。”赵辉表示,若无法给出明确解释,可把多种可能性都摆出来,如实反映现象即可。陶寺工作量之多、难度之大,可见一斑,对发掘者能沉下心来琢磨地面情况、空间关系、层位关系表示敬佩,也期待距离陶寺的真相能更近。
 参观遗址
参观遗址
“8000平方米范围轮廓的形成过程是怎样的?基坑夯筑的过程是什么?版筑的方法怎样?做解剖或许会对带来清晰地认识。其次是位置问题,建筑位置偏宫城东南角、非中心位置。F40面积不大、但相当精致,也不排除其特殊功能区的定位。陶寺遗址难发掘,也正是因为它的重要性,每一个已知线索都要利用好又不能轻易挖掉。”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李新伟研究员在发言中谈到。
用建筑的眼光重新打量陶寺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宋江宁研究员表示,古代建筑知识体系的全面考量是必要的。生土概念并非学科概念,他建议在发掘中扔掉生土的概念,这对认识和研究古代建筑起到作用。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马晓教授在发言中谈到了对建筑体系和柱网两方面的疑惑。两种不同建筑结构体系在此混杂,主殿建筑为木构架承重,周围则是夯土承重,两种风格截然不同。建造时间和次数问题可能导致主殿建筑存在柱洞缺失、错位等现象。“建筑考古所关注的是柱洞、磉礅等,而建筑关注的是上部结构。两者之间有被忽略的部分。应当通过复原研究把这一问题解决。”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林源教授表示,建筑发展的陶寺阶段尚处于幼年时期,或许尚未达到考虑结构形式和做法的阶段、也无需刻意考虑轴线问题。需要着重关注的是通过什么控制建筑组群和之间关系以及夯筑的顺序。
保护工作 刻不容缓
陶寺遗址自1958年被发现,1978年启动发掘。数代考古工作者呕心沥血、辛勤耕耘,尽管已历经40余年,但陶寺遗址的每次考古新发现都会引起学界的关注和重视。考古发掘非一日之功,陶寺遗址的保护工作刻不容缓。如何最大限度地保护好、利用好陶寺遗址,也成为无数专家最关心的问题。

长期保护任重而道远,项目负责人高江涛心里也没有十足把握,“为了保护F40我们在上面洒了一层十多厘米的黄沙。但也知道这根本经不住长期的风霜雨雪、日晒雨淋。”高江涛回忆到。陶寺出土的众多精美文物早已移交博物馆,但考古现场保护却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包括采用什么样的理念和技术进行保护,保存下来的考古现场如何展示等。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王晓毅直言:“需要搭大棚保护!”
知多惑多的“硬货”
站在陶寺的土地上,无数考古专家也发出“陶寺的土太难认!”的感叹。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王芬教授就表示“四年时间揭示出一个台基面。如此大体量、土里找土,确实不容易。”会上,王芬还就最初原始地貌形态、台基建造过程、土壤微型态取样等问题提出意见与建议。社科院考古所刘瑞研究员除了认同在土壤学分析上进行深入探索外,还提出在大型建筑旁寻找水井的建议。
“1983年的秋天我第一次来到陶寺,一晃快四十年了。此次大型建筑基址的发掘,历经4年时间、发掘5400多平方米,尽管遗迹不复杂,出土遗物少、破坏严重,很多东西都展现在一个面上,导致相互关系判断不易。”长年关注陶寺考古的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栾丰实教授感慨道。他总结发言中指出,陶寺遗址在中国文明起源阶段到早期发展阶段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参观遗址
参观遗址
基于陶寺遗址扎实的基础工作
学者在此次会议上基本达成以下共识:
规模恢弘——在这一时期,对于8000多平方米的夯筑建筑来说是罕见的、唯一的。
范围清楚——不仅整个遗址和宫城范围清楚,在勘探与发掘基础上该建筑的四至也清晰。
时代明确——建筑和台基在陶寺中期建成并使用、于晚期被毁,年代局限在较小的时间范围之内。
栾丰实还指出整个8000平方米的台基是如何形成的?其基座是否存在?对于台基的形成过程还要做进一步工作。包括台基和主殿夯筑方法是否一致等。台基上陶寺中期遗迹很多。尤其是保存状况好的房址,其相互年代关系的判断必须在田野完成。地层学划分年代的尺度比类型学更加细致,聚落考古提升了地层学里共时关系的认识。遗迹间的相互关系、共时性问题必须在田野阶段解决。栾丰实强调,解剖是必要的。首先要充分利用被破坏的晚期遗迹,试图做到最大限度的利用,并尝试进行复原式解剖。在遗址保护问题上,如精致的F40地基础保护工程都亟需落实,为日后遗址公园建设、文物保护示范工作做充足准备。

诚如陶寺遗址发掘者高江涛与何驽所言,多年来专家的宝贵意见为陶寺的发掘与研究提供了极大帮助。“这是一块难啃的‘骨头’,也是真正的考古‘硬货’。”
脚踏实地的求索,是无数考古人步步前行的真实写照。遇到陶寺,就需要长期付出;在陶寺,也让人感受到坚守与情怀的无处不在。
古代哪里的女孩子最喜欢穿木屐?白嫩的脚露出来,李白眼都看直了
古人喜欢什么样的凉鞋本文作者倪方六眼下正是炎热的季节,凉鞋成为大家出行的首选。在古代,人们夏天也喜欢凉鞋,其中以木制凉鞋最受欢迎。图:清末制集木屐摊过去老百姓夏天所穿最多的,便是木制凉鞋了。木制凉鞋,古人称为“木屐”。我要新鲜事2023-05-27 13:33:180000高考状元为何三次入狱?父母悔恨道:儿时教育忽视一个重要环节
高考可谓是人生的一道“分水岭”,“读书无用论”随着时代的进步,这个观点一次次遭到打脸。原本出生贫寒的学子,通过高考实现人生逆袭的案例比比皆是。百度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李彦宏,是山西省阳泉市的高考状元。京东创始人刘强东是江苏宿迁的高考状元,巨人网络史玉柱是安徽怀远县的高考状元。如今这三位网络大亨都已身价过百亿,活生生的被那些抛出读书无用论的父母,狠狠打脸!我要新鲜事2023-05-25 10:20:460000崇高龙:阿根廷大型食肉恐龙(长8米/距今1亿年前)
说到恐龙,食肉恐龙总是更受人关注,如今各类影视作品中,也更喜欢刻画食肉恐龙,比如霸王龙、食肉牛龙等。而今天小编要介绍的也是一种食肉恐龙,它就是崇高龙,出土于阿根廷,一起去认识看看。崇高龙基本资料崇高龙是一种南美洲的大型食肉恐龙,它长6-8米,与阿贝力龙、楯甲龙差不多大,体型暂时在已知774种恐龙中排第234位,生活在距今1.12亿-1亿年前的早白垩世。崇高龙化石我要新鲜事2023-05-09 07:11:520001十大深度解读 | 李新伟:中华文明起源的多元场景
#十大考古#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入围终评的新石器时代项目中,长江流域有二,浙江井头山遗址入选;黄河流域占三,河南双槐树和时庄遗址入选,在中国考古学百年之际,为诞生之地献上厚礼。但“中原”之大胜,并不会让我们重归“中原中心”的旧路,新发现揭示的是中华文明自孕育之初就呈现出的多元发展的鲜活场景。我要新鲜事2023-05-07 17:49:430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