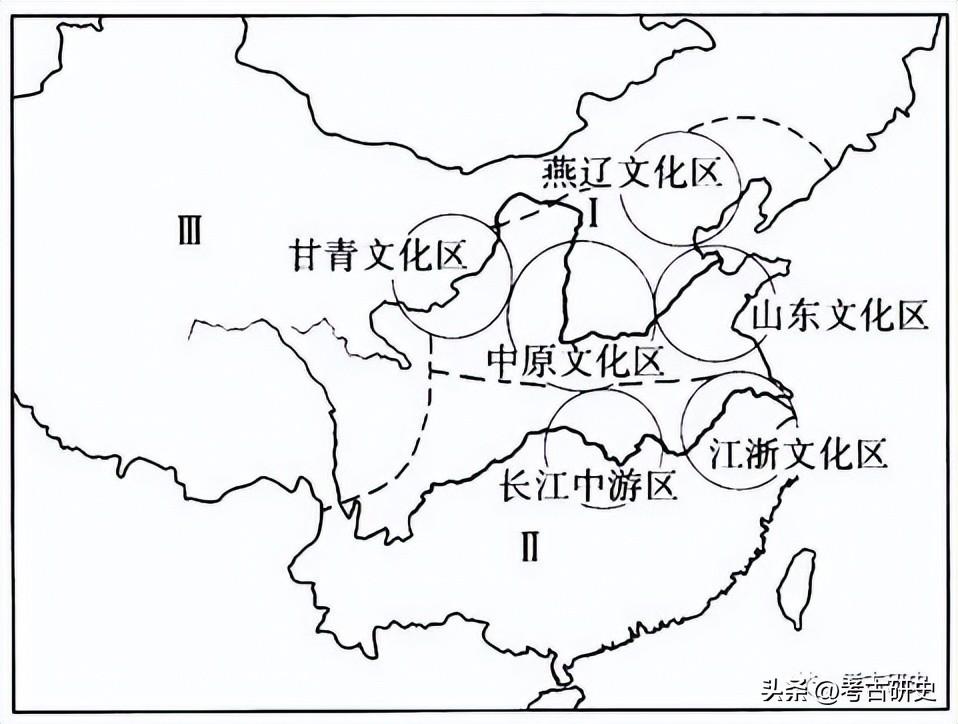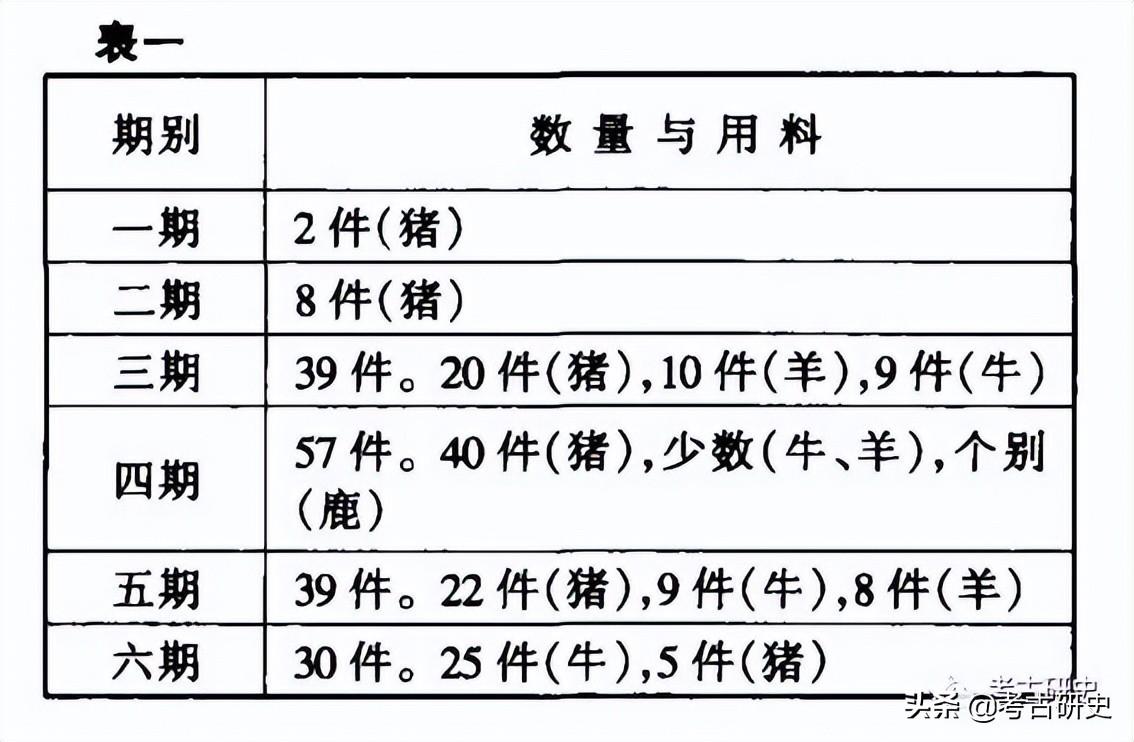王仲殊:关于日本第七次遣唐使的始末
(一)
7 世纪末通过藤原京的建造和大宝律令的制定等而在内政上做出很大业绩的日本朝廷,接着谋求在外交方面也取得与此相应的成果。
自天智天皇十年(公元671年)以来,与中国的交往已中断达30 年之久。随着日本国力的增大和东亚国际形势的转变,恢复日中关系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就在大宝律令编篡完毕的同时,便作出了重新派遣遣唐使的决定。
文武天皇大宝元年(701年)正月, 新的遣唐使团人员组成已安排定当。执节使(权位在大使之上)为粟田真人,大使为高桥笠间,然后是坂合部大分为副使,许势祖父为大佑,鸭吉备麿为中佑,扫守阿贺流为小佑,锦部道麿为大录,白猪阿麿、山上忆良为少录,垂水广人为大通事(翻译宫)。只因高桥笠间另有任用(翌年八月任造大安寺司),坂合部大分升任为大使,副使之职则由巨势邑治充当。自舒明天皇二年(630年)以犬上御田锹为大使的第一次遣唐使访唐以来, 这是第七次遣唐使(天智天皇六年以伊吉博德为首的使团送唐驻百济镇将刘仁愿所遣使者司马法聪至百济而还,未往中国,不算是正式的遣唐使)。
除上述各主要职官以外,参加第七次遣唐使团的其他人员有谁,这在《续日本纪》中亦无明确的记载。但是,参照《续日本纪》所录元正天皇养老三年(719年)十一月朔日的诏书及《扶桑略记》的记述, 可确认著名的僧人道慈也随第七次遣唐使前往。此外,在《万叶集》中可见三野连(“三野”为氏,“连”为姓,其名失记)赴唐时春日藏首老为其送别而作的诗歌中有“对马之渡”的字句,从1872年在奈良县平群郡获原村发现的美努连冈万的铜质墓志可以判断,三野连即为美努连冈万(在日本语中,“三野”与“美努”读音相同,皆为“mino”)其人。墓志明记美努连冈万于大宝元年五月“使乎唐国”,故可认定此人亦是使团中的一员。
关于第七次遣唐使的规模,即船舶数和人数,史书无明确记载。西本愿寺本等《万叶集》校本在对上述春日藏首老的诗歌所作附记中谓“国史云,大宝元年正月遣唐使民部卿粟田真人朝臣以下百六十人,乘船五只”。但是,此处称为“国史”的书籍成书年代甚晚,所记不足为信。从此前、此后派遣的遣唐使的规模推测,这次遣唐使团总人数至少在二百人以上,所乘船舶在二艘到四艘之间。
当时粟田真人任民部尚书之要职,初任时的官位为“直大贰”,随着大宝律令的实施而改为“正四位下”(相当唐的正四品下),有奉敕参议朝政的资格。他是编篡大宝律令的主要成员之一,学识渊博,颇有声望。要之,从人数和船舶数看来,第七次遣唐使的规模未必有以后各次遣唐使那样大,但从执节使的官职、名位而论,此次遣唐使在政治上的规格甚高。著名的诗人学者山上忆良任少录,翻译官大津广人被赐以“垂水”之姓,而精通佛教经典并擅长各种技艺的道慈法师则作为留学僧而同行,凡此种种,皆足以说明在相隔30年之后而重新派遣的这次遣唐使甚受日本朝廷的重视,使团成员中包含着许多出色的人才。
这里,必须提到的问题是,以粟田真人为首的第七次遣唐使是否持有国书。如所周知,从江户时代的本居宣长以来,认为遣唐使不持国书的见解长期在日本学术界占支配地位,几乎已成通说。然而,东京大学名誉教授西岛定生先生在其《遣唐使与国书》的论文中则以中国唐朝丞相张九龄文集所收称为《敕日本国王书》的唐玄宗的敕书(张九龄起草)为主要依据,并经对各种史料的细密考究,得出了与上述通说相异的结论,明确主张遣唐使是携有国书的。我相信西岛先生的见解是正确的,从而认为粟田真人是携着国书赴中国的。我觉得,作为来自外国的使臣,粟田真人若无国书在手,那末,他不仅不能在都城长安、洛阳觐见中国的皇帝,其所率领的使团全体人员甚至将不得允准在中国入境。
(二)
从大宝元年(701年)正月任命以后,经过三、四个月的时间, 使团出发的准备大体上已经完了,故于同年四月十二日举行“拜朝”,五月七日又举行“授节刀”的仪式。由于美努冈万墓志中有“五月使乎唐国”之语,可推测在各种仪式完毕之后,粟田真人迅速率使团离开都城藤原京,从难波(今大阪)经过濑户内海,直趋筑紫(今九州福冈县)。从当时一般的行程推测,到达筑紫的时间应在同年初秋。但是,从筑紫港口开船之时,遇到暴风雨,以致出发的日期不得不延至次年(702 年)六月二十九日。当时,百济、高句丽早已相继灭亡,统一朝鲜半岛的新罗恃其强大的国力,严密控制水陆交通。这样,第七次遣唐使不得不改变航行的路线,南下经南岛诸岛(今冲绳的琉球列岛等)而往中国。春日藏首老按照过去航行的惯例,在美努冈万受遣入唐时所作诗歌中有“对马之渡”之语,这是不符事实的。
海路上经常遇到各种困难和危险,但第七次遣唐使的航行却十分顺利。六月末从筑紫出发以后,不满2个月,便到达中国的楚州。楚州的辖境包括今江苏省淮河以南、盱眙以东、宝应以北的地区。据《续日本纪》记载,粟田真人在楚州的盐城县入境之时,才知道武则天已于永淳二年(683年)即位称帝,其国号为“周”。按照当时的规定, 首先须在楚州的州治所在地山阳(今淮安市)办妥手续,然后前赴中国的都城,此乃通例。据《旧唐书·则天皇后本纪》记载,粟田真人于长安二年(702年)十月到达都城长安,可称是快速的行程。中国方面派五品中书舍人在长安附近的长乐驿迎接,宣敕劳问,优礼有加。
唐王朝采取“两京制”,长安为京师,洛阳为东都。武则天即皇帝位以来,加速了洛阳城的建设,并改称“东都”为“神都”。女皇帝在其在位的20年中,18年在洛阳宫中执政,当时的“神都”是中国实际上的首都。只是在临近最后的长安元年(701年)十月至三年(703年)十月的2年间,武则天移住京师长安。于是,粟田真人一行经过洛阳, 是在长安向中国朝廷呈述使命的。长安的宫城和皇城位于全城的北部中央,有着宏伟的规模。宫城称太极宫,其为皇帝居处的同时,亦是执掌朝政的场所,指向全国的各种政令都是从这里发出的。然而,建造于长安城北面东头的新宫大明宫于龙朔二年(662年)完成, 其规模视太极宫有过之而无不及。从此以后,皇帝移至大明宫,此宫遂取代太极宫而成为京师长安的政治中心。这样,与以往历次遣唐使多在太极宫觐见不同,粟田真人是在大明宫觐见则天武后的。
说到这里,我把话题转到古代日本的都城制度。天武十二年( 683年),天武天皇发布诏书,宣告都城不限一处,应造二处,日本学术界乃称之为“复都制”。但是,从字面理解,所谓“复都制”是指都城在二处以上,而诏书只规定都城应造二处。因此,我认为,与称为“复都制”相比,不如使用“两都制”之词更为妥切。我觉得,天武天皇以飞鸟地方的倭京为首都,以难波为副都,这是模仿中国长安、洛阳两京并列的制度。到了持统天皇八年(694年),藤原京营造完毕, 它取代天武朝的倭京而成为日本的新都。如所周知,藤原京和难波京都是按照所谓“条坊制”而设计的中国式都城。特别是首都藤原京,不仅在形制的总体上模仿中国的长安、洛阳,而且在都城内的“皇城”、“大极殿”、“朱雀门”、“朱雀大路”、“东市”、“西市”等的名称使用上也与长安城的各相应处所相同。长期在藤原京任职为官的粟田真人等日本使节团的成员们,看见憧憬已久的长安城的实况,在觉得欣羡的同时,想必会有发自内心的亲近感。
(三)
自7世纪60 年代初期在朝鲜半岛西南部百济的白村江口海上发生中日之战以来,到此时已逝去三十多年的岁月,东亚的国际形势有了很大的变化。百济和高句丽灭亡以后,新罗一跃而成为朝鲜半岛唯一的大国。作为新兴的国家,新罗勤于向过去的救主中国朝贡,以求友好关系的继续,但因其与中国境界相接,两国之间有时不免发生纠纷。与此相反,日本在白村江之战受挫之后,丧失了在半岛的全部势力,甘心于作为海东远处的一个国家而不在国际上卷入争端,其与中国之间也不再存在任何问题。要之,从另一角度上说,中国反而有与日本取得联系以牵制日趋强盛的新罗的某种可能性。因此,对于不畏艰险、远道而来的日本使节团,中国方面表示热烈的欢迎。对则天武后本人来说,广泛地接受外国使者的来朝,亦可显示治世之兴隆、昌盛,从而提高其在中国朝野的威望。
如所周知,自古以来,中国称日本为“倭”,称其使者为“倭使”。据《新唐书·东夷传》记述,唐高宗咸亨元年(670年), 经过白村江之战,河内直鲸作为第六次遣唐使的使者,曾向中国方面传述其国已改称“日本”。但是,由于河内直鲸是战败国的使者,其使命是忍受屈辱而向中国祝贺平定高丽,加之在陈述国内情况时有虚夸、隐瞒之嫌疑,中国方面认为他之所言是妄言,不予重视。与此不同,粟田真人是根据大宝律令的规定,以正式的日本国使臣的姿态出现于长安唐王朝的朝廷上,中国方面当然不得不刮目相看。
据《续日本纪》所述,大宝二年(702 年)粟田真人刚刚来到中国楚州的盐城县时,有人问他是来自何处的使者。粟田以“日本国使”相答,其人则谓“闻海东有大倭国”云云。中国朝廷早在咸亨元年(670年)之时已知悉倭国采用“日本”的新国号,只因在此后的30年的长时期内,日本方面断绝了遣唐使的派遣,以致远离都城的楚州人民不知此事。然而,从史书记载看来,粟田真人等到达长安,以皇帝武则天为首的中国为政者以及主管外交事务的鸿胪卿等官员,都不曾向粟田问及改国号之事。这充分说明,正如《新唐书·东夷传》所明记,中国朝廷知悉从“倭国”到“日本”的国号更改是在长安二年(702 年)粟田真人来访之前。此外,朝鲜的史书《三国史记·新罗本纪》亦记文武王十年(670年)倭国改国号为“日本”,而孝昭王七年(698年)前来新罗访问的使者则称“日本国使”,这正与上述《新唐书》的记载相合。
在天武天皇十三年(684年)制定的“真人”、“朝臣”、“宿弥”、“忌寸”、“道师”、“臣”、“连”、“稻置”等的“八色之姓”中,粟田氏被赐以“朝臣”之姓。按照日本方面的习惯,粟田真人的氏、姓、名的全称为“粟田朝臣真人”,或置姓于名之后而称“粟田真人朝臣”。但是,中国方面是以姓为先,所以《旧唐书·东夷传》称其为“朝臣真人”,“粟田”二字被删除,《新唐书·东夷传》称其为“朝臣真人粟田”,“粟田”二字被置于最后。个别中国的学者或有因不知日本古代的姓氏制度而误解“朝臣”二字为在朝之臣的,故在这里顺便叙明之。中国的隋王朝设“民部尚书”之官,唐太宗即位以后,因其名为李世民,乃以避讳而改称“户部尚书”。中国方面知粟田真人任民部尚书,相当中国的户部尚书,故《旧唐书》称其为日本国之“大臣”。
按照大宝令衣服令的规定,作为“诸臣”,官位为“正四位下”的粟田真人礼服为冠、深绯衣、白裤、绦带、锦袜、乌皮舄,朝服为皂罗头巾、深绯衣、白裤、金银饰腰带、白袜、乌皮履。《旧唐书》和《新唐书》皆记粟田真人戴进贤冠,其顶为花,分而四散,身着紫袍,以帛为腰带。如若粟田所着为“紫袍”,则显然与大宝令规定的“深绯衣”相异,《唐书》的记述或许有所偏差。反之,倘若两《唐书》的记述无误,则可以解释为出使中国的粟田真人受日本朝廷破格的待遇,被赐以“从三位”官员所着浅紫之衣而服用之。唐王朝的服制亦以紫色为尊贵,亲王及三品以上的大官始得穿紫衣。
在1971年陕西省乾县发掘的唐章怀太子李贤墓的壁画中,有着称为“客使图”的图画。图画中描绘中国鸿胪寺的官员接待外国使者的情形,故亦被称为“礼宾图”。在东壁的礼宾图中,有着三位来自外国的使者,处于中间的那位使者曾被推定为日本的粟田真人。但是,这位使者所戴之冠插鸟羽二枚,身着白色衣服,脚穿黄靴,显然与粟田真人的冠服相异。从史籍的记述和考古实物资料两方面推断,壁画中的这一外国使者应是朝鲜人无疑。李贤出生于永徽五年(654年),死于文明元年(684年),乾县的李贤墓则为神龙二年(706年)所筑造。百济、高句丽分别于显庆五年(660年)和乾封三年(668年)为唐所灭,故可判断壁画中的白衣使者实为新罗的使者。
(四)
中国的官员会见粟田真人,通过就各种事情与他交谈,深知其学问、修养不同寻常,甚为钦佩。所以,两《唐书》皆称真人好读经史,解属文,容止温雅,而加以赞赏。推想山上忆良和道慈法师亦以其渊博的学识及其对汉学的造诣之深而受到尊敬。通览中国历代史书,在言及来自外国的使臣时,像对粟田真人那样盛赞其人品优秀的事例是别无所见的。与6 世纪中叶梁王朝的萧绎(梁元帝)在《职贡图》中所绘倭国使者的粗陋形象相比,8世纪初年的粟田真人不仅衣冠楚楚,风貌堂堂, 而且是才华出众的学者。自圣德太子的时代以来,经过大约百年间的政治、经济的不断改革,日本国的学术和文化的水平已提高到令人吃惊的水平。
如前所述,据《旧唐书·则天皇后本纪》记载,粟田真人一行到达京师长安的时间约在长安二年(702年)的十月, 而同书《东夷传》则记长安三年(703年)武后在麟德殿设宴款待粟田等。粟田等人到长安,受到中国方面的接待,恐怕还可能于翌年(703 年)正月元旦在含元殿参列朝贺的仪式。这样,其在麟德殿与武后的会见自应在长安三年(703年)元旦以后的正月某日。虽然在正月以后的可能性不是完全没有,但决不会迟于九月。与则天武后会见终了,立刻出席盛大的宴会。麟德殿在大明宫的西部,通过1957年以来的考古发掘,其形制、规模已被究明。全殿南北长130米,东西宽80米,三座殿堂分别建在前部、 中部和后部,两侧又加筑楼、阁,周围绕以回廊,建筑物的总面积广达13000平方米。皇帝经常在麟德殿举行集会和宴会,并在此殿会见各外国的使者。唐代宗于大历三年(768年)在麟德殿飨宴神策军将士, 人数竟达三千五百人之多,足可推想此殿规模之如何宏大。以执节使粟田真人为首,大使坂合部大分、副使巨势邑治乃至少录山上忆良和留学僧道慈法师等人,一同在麟德殿朝见中国女皇帝之后,出席了宴会,其场面的盛大可想而知。
聪明而通情达理的则天武后深知日本国的独立自主的政治原则,故按数十年来的旧例,不强加册封于对方。只是为了表示友好之意,特授粟田真人以司膳卿之职。按照大宝令公式令《集解》,日本规定以中国为邻国,两国的关系是完全平等的。但是,使臣个人被中国皇帝授以官职,这与对等外交的原则不相违背,故粟田真人欣然从命,不作推辞。唐王朝沿袭前朝的旧制,设光禄寺之官以掌管皇室的祭品、膳食乃至酒宴接待等事。高宗龙朔二年(662年),光禄寺改称司宰寺, 则天武后时又改为司膳寺。司膳卿的官位为“从三品”,大体上与粟田在本国任“正四位下”民部卿的官位相当,且稍为高出,以示尊重。总之,粟田真人率领的第七次遣唐使在长安顺利地完成了使命,在开拓日中交往的更为宽阔的道路的同时,将两国的友好关系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此次访问中国能取得如此重大的成果,除有国际形势的大局所趋作为其背景以外,与粟田真人个人的才能也是分不开的。
据《续日本纪》记述,粟田真人于文武天皇庆云元年(704 年)七月一日归国,这大概是指抵达日本的筑紫而言的。在长安三年(703 年)受到则天武后接待前后,粟田等在长安停留颇久,对京师的街坊、商市、佛寺乃至曲江池等名胜处都作过参观,并广泛结识各方面的有识之士,进行交流,在学问上大有进益。他们归国时途经洛阳,对神都的规模和建筑设施的布置,以及历代的名胜古迹之类,想必亦加以充分的考察。
(五)
庆云元年(704年)十月九日, 粟田真人在藤原宫作归朝述职报告。由于功绩出类拔萃,日本朝廷特于十一月四日赐田二十町、稻谷千斛,以为奖赏。翌年(705年)四月,粟田被任命为中纳言, 其官位亦于同年八月由“正四位下”提升到“从三位”。这样,他便成为日本朝廷决策集团的成员之一。此外,作为对经历危险的海上航行而得平安归国的庆贺,遣唐使所乘名为“佐伯”的船亦被授以“从五位下”的官位。以没有官位的少录身份随从粟田真人入唐的山上忆良,其归国后10年间的经历虽因史籍失记而不明,但从元明天皇和铜七年(714 年)被授以“从五位下”的官职看来,这或许也可认为是他在参加第七次遣唐使而入唐期间的良好表现终于受到肯定的结果。
1972年3月,在奈良县高市郡明日香村发掘了高松冢古坟。古坟中的壁画内容丰富,彩色美丽,绘描精致,被视为日本考古学上空前的大发现。在出土的随葬品中,有一枚称为“海兽葡萄镜”的铜镜,制作精良,保存状况甚佳。另一方面,早在1958年,在中国陕西省西安市东郊发掘了一座唐墓,墓志明记被葬者名为独孤思贞,他于武则天万岁通天二年(697年)死去,翌年神功二年(698)入葬此墓。在独孤思贞墓的许多随葬品中,也有一面保存良好的海兽葡萄镜。高松冢的海兽葡萄镜与独孤思贞墓的海兽葡萄镜相比,可确认两者属“同范镜”无疑。我以此事为主要依据,从多方面加以考证,认为高松冢古坟的海兽葡萄镜是以粟田真人为首的第七次遣唐使从中国长安携归的,而古坟的被葬者则为庆云二年(705年)死去的忍壁皇子,即刑部亲王。要之, 这面珍贵的铜镜是在庆云元年(704 年)十月初旬前后由归国的粟田真人作为礼物而赠送给刑部亲王的,后者于次年庆云二年(705年)死去, 此镜乃被作为随葬品而纳入坟内。从考古学方面而言,高松冢的海兽葡萄镜与前述美努冈万的墓志一样,都是直接与第七次遣唐使有关的重要文物。
元明天皇和铜元年(708年)十二月, 平城京的营造工程全面开展。与旧都藤原京相比,平城京的设计有不少新的特点。归纳起来,第一是对唐的都城长安、洛阳的模仿程度加强,从某种角度来说,其对长安城的模仿程度以“彻头彻尾”的形容词相加,亦不为过。第二是唐长安城在北面东头增筑大明宫,受此影响,平城京的全城平面和宫殿的配置亦不完全拘泥于左右对称的格局。此外,更进一步而论,从建筑形式看来,平城宫内的主要建筑物大体上都是仿照大明宫内宫殿而营造,特别是第一次大极殿的可称“龙尾坛”的大坛仿自大明宫含元殿特有的“龙尾道”,可传为古代中日两国建筑史上的美谈。平城京之具有上述那样的特色,其背景在于第七次遣唐使对中国都城的访问考察,这应该是没有疑问的。
执节使粟田真人等于庆云元年(704年)先行归国, 而大使坂合部大分、副使巨势邑治及僧道慈等则留在中国,继续从各方面作考察。据《续日本纪》所记,巨势邑治于3年后的庆云四年(707年)归国,而坂合部大分与道慈则迟在元正天皇的养老二年(718年)才随以多治比县守为“押使”(相当于执节使,权位在大使之上)的第八次遣唐使团而返回日本。道慈在中国留住时间长达18年之久,通过对佛教的修学,获得许多成果,贡献甚大。正因为如此,元正天皇特于养老三年(719年)十一月朔日发布诏书而称赞说:“道慈法师远涉苍波,窍异闻于绝境;遐游赤县,研妙机于秘记”,云云。据《扶桑略记》等记述,道慈在长安录取西明寺的建筑设计图样,平城京大安寺的营造即以此图为依据云。
养老元年(717年)作为第八次遣唐使团成员之一的吉备真备, 在中国留学凡17年。推想在最初的半年多的时间内,吉备真备在长安与道慈会见,听取道慈在中国留学的经验。当然,从学问的分野而言,以佛教的修学为主的僧人道慈与广泛研究政治经济、律令制度以及各种文化事业的留学生吉备真备相比,二者的性质颇不相同。但是,我想,在8世纪初期,假若没有为恢复日中关系而尽力、为两国交流的进一步发展而开拓道路的第七次遣唐使的成功,随着第八次遣唐使入唐而在中国长期留学的吉备真备是不可能取得那么辉煌的成果的。
说到这里,我想把以下的事情作为一段插曲而述及。据《旧唐书》和《新唐书》记载,在第七次遣唐使执节使粟田真人归国的次年(705年),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则天武后以82岁的高龄逝世。武后在其作为皇帝而在位的20年中,会见了诸多来自外国的使者,而日本的粟田真人则是其中的最后一人。推想粟田对武后深怀感激之情,故将武后为显示其作为皇帝的威光而创制的所谓“则天文字”传入日本。这里冈山县小田郡矢挂町出土的吉备真备祖母的铜质骨灰盒上有相当详细的铭文,而吉备真备(本姓“下道”,圣武天皇天平十八年即公元746 年十月赐姓“吉备”)之父下道圀胜及叔下道圀依的名字见于铭文中,乃可认为他们二人或许是日本最早使用“则天文字”者。骨灰盒铭文记其为元明天皇和铜元年(708年)所制作, 而正仓院所藏含有“则天文字”的《王勃诗序》则抄写于文武天皇庆云四年(707年),故可推定“则天文字”是由庆云元年(704年)归国的粟田真人传入日本的。在一千多年以后的江户时代前期,水户的副将军德川光圀声望极高,其名字中亦有属于“则天文字”的“圀”字,则是无人不知的。
今天,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在这里吉备真备故乡所在地讲述日本古代的遣唐使之事,在怀念其可贵的业绩的同时,衷心祝愿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经久不绝,万古长青。
(附记:本文为1993年7 月作者应邀在日本冈山市就实女子大学所作公开讲演的全文,由作者本人执笔的日文原稿刊载于1994年发行的《就实女子大学史学论集》第9号)
来源:《考古与文物》2000年第3期
浙西南古村落保护利用水平的不同层级及改良建议
浙江西南部的金华、衢州一带,聚落型文化遗产资源丰富,留存下很多完整的古村落。但是,其中的各县区、各乡镇、各村寨,因其地理位置、交通条件、建筑风格、文化传统、社会观念、政府决策等方面的不同,而使其保护和利用的状况显现出不同层级的差异。本文以衢州衢江地区和金华兰溪、浦江地区的古村落为例,对浙西南古村落特点及不同层级的保护利用状况进行探讨。浙西南古村落的建筑风貌特征我要新鲜事2023-05-06 16:46:100003西北政法大学挖出古墓,墓主人是西汉酷吏,专家:挖到了祖师爷
古墓的发现一直是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们关注的焦点之一,每一座古墓都承载着一个时代的记忆和历史的传承。近日,西北政法大学挖出了一座汉武帝时期的墓葬,墓主人竟然是著名的酷吏张汤,这让人们对这个历史人物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我要新鲜事2023-04-22 03:22:190009郭静云教授答沈长云先生的信——并简要回复许宏先生的评论
【编者按】自郭静云教授《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一书出版一来,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和争论。现受郭静云教授之托,刊发郭静云教授回复沈长云教授信件全文。感谢光明日报转来沈长云教授的信函。更多谢沈长云教授用心讨论拙著,对此本人感觉到很荣幸。因为拙著篇幅确实很长,沈先生来不及在短期时间内看得仔细,所以本人针对沈先生提出的一些问题说明如下:0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