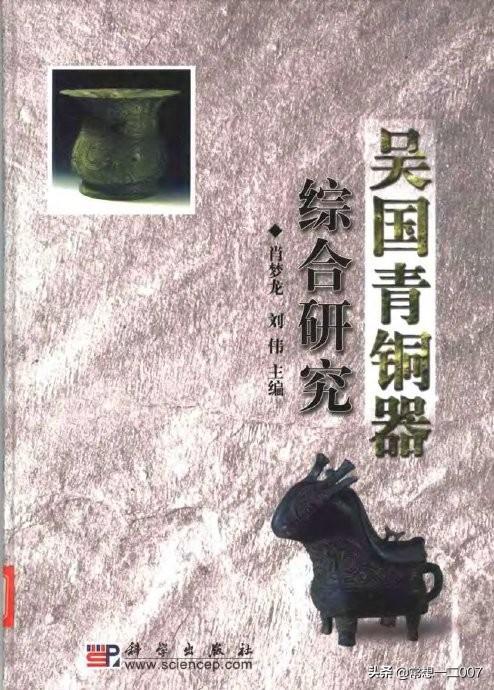王明珂:论攀附:近代炎黄子孙国族建构的古代基础
#头条创作挑战赛#本文很长但也很重要很精彩,建议收藏有空慢慢品。
本文说明近代以“黄帝”或“炎黄”为共同祖源想象的中国国族建构,是一沿续性历史过程的最新阶段。在战国晚期的华夏认同中“黄帝”已成为此一群体之共祖,并蕴含领域、政治权力与血缘之多重起源隐喻。这样一个浑沌初成的族体,在战国以来透过人们攀附“黄帝”(或炎帝)及其后裔,逐渐在两种“华夏边缘”扩张——政治地理的华夏边缘,以及社会性的华夏边缘。透过“得姓”以及与姓相链接的祖源历史记忆,愈来愈多中国周边非汉族群的统治家族,以及中国域内的社会中下层家族,得与“黄帝”(或炎黄)有血缘联系。最后在此基础上,以及在国族主义蕴含的个人主义精神上,晚清民初中国知识分子终于将黄帝与“每一个”中国人系上此血缘关系。本文并以近代北川羌人汉化的例子说明,邻近群体间相互的夸耀、歧视与模仿、攀附,是推动此华夏边缘扩张的重要机制。
以此,本文强调近代国族建构自有其古代沿续性基础。“黄帝攀附”便代表由华夏蜕变为中华民族过程中沿续的一面。而近代国族建构中最重要的想象、创新,与因此造成的与“过去”之间的断裂,应导致于语言学、体质学、民族学与考古学在国族建构中之运用。

黄帝、炎帝及相关的古代“民族集团”,在二十世纪上半叶曾是中国上古史研究中的重要主题。当时在新的史学与民族学概念下,黄帝被认为是一个来自北方或西方的民族集团首领,炎帝则被认为是同一民族集团中曾与黄帝争胜的另一支族首领。民族学的图腾说,也被用来支持这些上古的“历史事实”;黄帝等被认为是“龙”图腾的部族,相对于东方以凤鸟为图腾的太皞等部族。略晚,殷墟发掘与相关古文字与古史的探讨,为后来的中国上古史研究开创了一条康庄大道——“科学史学”从此成为史学研究主流。此后中国历史学者的注意力很少及于夏代之前。更不用说,除了一些非学院的研究兴趣外,“黄帝”也被认为是属虚无飘渺而乏人问津了。他被归类于“神话人物”,或如顾颉刚所言,层累造成的神话的一部分。“神话”相对于强调“真实过去”的历史而言,被认为是虚构、想象的,因此追求“史实”的学者们自然对此不肖一顾。
然而例外的,近代史研究者沈松侨先生近年发表一篇有关黄帝的论文。这篇文章的研究角度,完全不同于二十世纪上半叶研究古代民族集团的历史学者之观点。简单的说,无论是采血缘主义或文化主义,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学者强调的都是以黄帝为共同起源的延续性历史;一个“起源”沿续为当今血缘与文化上的中国人,或中华民族。沈先生所强调的却是“历史”的断裂、创造与想象;黄帝,一个过去的皇统符号,在近代国族主义(nationalism)下被中国知识分子集体建构为中国人的共同祖先。沈先生引了大量清末民初史料,说明在西方国族主义的冲击下,部分汉人(与少数满人)知识分子,包括革命派与立宪派人士,选择、想象黄帝为所有中国人的祖先。这个研究说明,许多近代学术活动都是“国族主义”下的集体回忆。在此集体回忆中,民族“始祖”与其他“民族英雄”被选择、塑造,以应和国族建构与凝聚国族认同。我认为,无论是对于中国国族主义下的古史建构,或是以新方法探求史实,沉着都是一篇重要的论文。
熟悉西方当代学术潮流者,对这样的研究取向应不陌生。社会学与人类学有关记忆与认同的研究,曾引发西方历史学者对近代国族认同与相关文化建构的讨论。学者指出,当代人们认为是相当老的国族,其实是国族主义下知识分子集体建构的“想象群体”;一些被认为是“古老的”传统文化,也经常被认为是近代国族认同下的文化建构。依循“想象群体”与“传统建构”之论述模式,近年来有些西方历史与人类学者也以此解构“中华民族”、“中国少数民族”,以及相关“历史”或“民族史”的近代建构。“黄帝子孙为晚清中国国族建构下中国知识分子集体想象”之说,便是此种分析模式下之产物。
我们可称之为一种“近代建构论”。持此论之学者,认为在近代国族主义与相关学术知识(民族学、语言学、体质学等)的引领下,世界各地都曾发生一个“国族化”(及连带的现代化)过程。我们当前的国族认同,以及国族下的民族区分,以及相关的语言、体质、民族与历史知识,都在此过程中被建构起来。重溯此建构过程,可说是一种“后现代”(post-modern)醒觉与认知下对“近代的”(modern)国族与相关知识的解构。然而,“近代建构论者”只是解构近代以来被建构的“历史”与“国族”,他们或完全对“古代史实”毫无兴趣,或将“近代以前的历史”简化为一同质的、停滞的状态。如此一个同质的“古代”突显了近代的变迁——也因此,在许多学者眼中“中国国族”在近代以前是不存在的。
此种理论原来便有以“近代”割裂历史延续性的缺失。历史学者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曾对此提出批评。他指出,近代国族是历史上各种不同的、相互辩驳的论述,与近代国族国家体系之间的对话与妥协产物。事实上,“黄帝后裔”或“炎黄子孙”便提供了一个探究此问题的绝佳场域。沈松侨先生在前引文中也承认,先秦以来,华夏及其周边人群常试图假借黄帝来改变“中国”的族群边界。Patricia Ebrey研究“姓”与“汉人认同”之关系;她指出,由于得“姓”及一可溯及著名远祖的家族历史,许多非汉人群在历史上成为汉人。她也提及,在唐宋时期,这些家族历史中最后被溯及的始祖常是炎帝与黄帝。因此她认为“追溯黄帝为始祖”,并非如部分学者所认为起始于二十世纪中国国粹派史家,而是此始祖意象在中国已有很长久的历史。[1]我认为这是篇值得重视的论文;不仅指出近代之建构自有其古代基础,更重要的是,表现一种历史人类学的“汉族”研究——以“姓”与家族记忆当作一种“土著观点”,以各种史料与族谱作为田野以探索“汉人”的本质。
近年来,我一直在文献与当代羌族两种田野中作研究。我所从事的研究,是从“历史记忆”中探索羌族、汉族与中华民族的本质,及相关的历史变迁。这也是对“华夏”或“中国人”的一种边缘研究;由华夏边缘的形成与变迁,来探索华夏或中国人的本质。在本文中我将以中国家族记忆的发展,来探讨“炎黄子孙”族群意象的历史变迁,藉此也对我自己由边缘理论解释华夏形成与变迁的“华夏边缘”之说作一实证与补充;以及,作为对沈著及Patricia Ebrey 文的续貂之作。简单的说,我认为在汉代或更早,黄帝的确只与帝王或少数古帝王族系有关。然而在战国时及此后,由于一种普遍的心理与社会过程——攀附——在“血缘”记忆或想象上可与黄帝联系上的人群逐步往两种“华夏边缘”扩张:政治地理的华夏边缘,以及社会性的华夏边缘。最后,在此历史记忆与历史事实基础上,并在国族主义影响下,晚清知识分子终于将黄帝与每一个“中国人”系上想象的血缘关系。也就是说,清末诸贤的确受西方国族主义之影响,重新集体回忆黄帝并赋予新的意义,以创建中华民族。然而,如果不以“近代”断裂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族群想象”可以经历两千年而形成当代的“炎黄子孙”。
这篇论文的主要目的并非反驳“近代中国国族建构”之说。相反的,我同意近代的确有一国族建构与相关文化建构过程。本文只是以“炎黄子孙”为例说明,“古代”并非如近代建构论者所认为的“同质”;所谓“近代建构”只是长远的历史建构与想象的一部分,而近代“中华民族”之形成,也基于一长远的“族群形成过程”(ethnic process)。藉此,相对于后现代主义学者注意的历史断裂与建构,我强调一种历史的沿续性。这个历史,自非是国族主义下的历史,而是一个“华夏边缘”研究角度下的历史。
黄帝出现在中国文献记忆中,较可靠的时间大约是在战国时期。西周金文中追美祖先,最多及于文王、武王;春秋时的齐国器叔尸钟,才提到成汤、禹。战国时齐国器,陈侯因资簋,其中才出现“高祖黄帝”之语。在成书于战国至汉初的“先秦文献”中,黄帝逐渐广泛被提及;其多元本质也在这些相关述事中出现、开展。起先,他在许多文献中都是一古帝王,与伏牺、共工、神农、少皞等并举,并未有各个氏族或部族共同祖先之意。然而到了汉初司马迁写《史记》时,黄帝已成为他心目中信史的第一个源始帝王,且为夏、商、周三代帝王家系的共同祖先了。这正是许多学者都曾注意的,黄帝多重面貌中的两面——某些家系的始祖,以及,统治一时代或诸部族的帝王。黄帝如何在战国到汉初之间,由众帝王之间脱颖而出,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
我们可以将战国至汉初的中国古文献皆视为一些社会记忆,由其述事之文本变化中探索“黄帝”之多元隐喻,及影响这些社会记忆的社会情境(social context)及其变迁。首先,在许多战国至汉初的文献中,黄帝只是许多古帝王之一;他代表统治一个部族或一世代的帝王。如《左传》中记载,春秋时之郯子记述各个古帝王氏族;其中“黄帝氏以云纪”,相对于以火纪的炎帝氏,以水纪的共工氏,以龙纪的太皞氏,及以鸟纪的少皞氏。以此而言,黄帝只是许多部族首领之一,未有特别之处。然而,另一文献《国语》则称:“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这是直接以黄帝作为虞、夏、商、周四代帝王家族的共同祖先了。
在有些文献里,这些古帝王被排列在线性的历史中。在《管子》一书中他是许多受天命而得封禅的古帝王之一。在同书另一篇章中,黄帝也是开化天下的古帝王之一;前有虙戏、神农(或亦有燧人),后有夏、殷、周人。于此,以及类似记载中,黄帝的象征意义都是:相对于美好纯朴的古代,他代表一个较复杂的近代世界之始。如在《商君书》中,相对于“男耕而食,妇织而衣”的神农世代,黄帝则“作为君臣上下之义,父子兄弟之礼,夫妻妃匹之合;内行刀锯,外用甲兵”。《周易》中则记述一个人类文明进化过程;“黄帝、尧、舜”代表“后世圣人”,出现于古代或上古的包牺氏与神农氏之后。在这些文本中,黄帝皆隐喻着文明开创者之意。《庄子》中所载“昔者黄帝始以仁义撄人之心”;也是以黄帝来指涉一个新世界的开端。虽然对老庄者言,这也是混乱腐败世界的开始。
黄帝在战国文献中的另一意象则为,以战事、征伐平定天下的帝王。如在《左传》中记载,有卜者得“遇黄帝战于阪泉之兆”,此兆为有利于军旅之事。《庄子》之中也有记载称,黄帝不能遂行德业,而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更多的战国文献记载黄帝与炎帝之战事,如《淮南子》所载:“兵之所由来者远矣,黄帝尝与炎帝战矣,颛顼尝与共工争矣。”其它如,《列子》中记载称“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帅熊、罴、狼、豹、貙、虎为前驱,鵰、鹖、鹰、鸢为旗帜”;《孙子》称“凡此四军之利,黄帝之所以胜四帝也”;《鹖冠子》中称“上德已衰矣,兵知俱起;黄帝百战,蚩尤七十二,尧伐有唐,禹服有苗……”等等,都将黄帝视为战事之代表与征服者,黄帝世代作为天下兵戎交征之始。
在战国文献中,最常与黄帝相提并论的古帝王便是神农,以及炎帝,或两者为一。前面所提及黄帝的几种角色,都与神农或炎帝有关。如神农或炎帝为先于黄帝世代的帝王,代表较原始、质朴或析乱的时代。如炎帝是败于黄帝之手的古帝王,黄帝因此也代表征服者,或代表一个大动干戈兵刀的时代。在《国语》之中,黄帝与炎帝又有较特殊的关系。《国语‧周语》中记载,鲧、禹与夏人之后,以及共工、四岳与各姜姓国,“皆黄、炎之后也”。根据此记载,黄帝与炎帝的后代都曾犯下错误,但也曾合作克服水患。《国语‧晋语》中记载,“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同文又称,黄帝、炎帝两人动干戈,就是因为两人异姓则异德,异德则属“异类”。因此在《国语》之中,黄帝与炎帝两系的关系是分立的(异姓、异德、异类),是合作的,同时也是对抗的。这样的关系,表明于此文献中所载炎、黄二人的“弟兄”关系之上。
我曾在川西岷江上游地区,研究当地羌族村寨中流传的“弟兄故事”。此种故事产生于特定社会情境,且有其结构化之述事方式。譬如,一山沟中有三个寨子,寨中村民说起本地三个寨子住民的起源时常说,“从前有三个弟兄到这儿来,他们分别成为三个寨子村民的祖先……”云云。我曾指出,“弟兄故事”是一种历史心性下的历史述事,以始祖间的“弟兄关系”来说明当前既合作又对抗的几个亲近村寨人群的“共同起源”。与此相对的另一种历史心性便是,以一“英雄祖先”为起源,并描述其征服四方经历的历史述事。
无疑,在战国时期,居于政治社会上层的历史书写者已被“英雄祖先”历史心性所掌控;这说明,为何我们在许多先秦文献中都常见到黄帝、炎帝、少皞、颛顼等等“英雄祖先”。然而,《国语》“晋语”中的这个记载似乎也说明,当时作者仍存有“弟兄故事”此历史心性,因而会创作出炎、黄为兄弟的历史述事。无论如何,我们知道在战国时知识菁英的认知中黄帝为姬姓;此自然由于姬是尊贵的周天子家族之姓。姬周与姜姓之族,又是姻亲,又是盟友,最后又是敌人;姜姓申侯勾结犬戎作乱,结束了西周在渭水流域的基业。这些,也是战国时人深刻的历史记忆。西周时期姬与姜之间亲近而又对抗的关系,或许便是《国语》相关篇章作者认为姬姓黄帝与姜姓炎帝为“兄弟”的历史记忆背景。无论如何,先秦文献中炎帝(或神农氏)与黄帝之间的亲近关系,其述事的寓意之一在于以炎帝来衬托黄帝的历史意象——以炎帝时天下之崩乱、原始、质朴,以及炎帝的传说性,相对衬托黄帝所代表的统一、文明、进步与其历史性。学者们常强调黄帝作为许多事物与人群“创始者”之意象。但我们不能忽略,当战国至汉初学者将炎帝(或神农氏)与黄帝相提并论时,黄帝也代表一种“当代”与“过去”之间的“断裂”。
在战国晚期五行说的影响下,黄帝又代表居于中央的土德帝王。如《淮南子》所载,相对于南方属火的炎帝以及西方属金的少昊等等,黄帝为居于中央之帝,属土,“其佐后土,执绳以制四方”。由黄帝之佐执绳以制四方看来,此时在“五帝”之中黄帝已居主宰地位。《庄子》中称:“世之所高莫若黄帝……。”——亦可见此时黄帝已有超越其它传说古帝王的地位。
无论如何,战国末至汉初,可说是许多“思想家”尝试整合上古诸帝王的时期。这样的作为,也是一种历史想象;其产生的社会情境与秦汉中国的政治统一,以及“华夏”认同的明确化,是密切相关的。也就是说,此时由于各地人群在政治与社会文化上的交流,由黄河中下游到长江中下游的“华夏”间产生了一体感。整合上古诸帝王,也就是将各地域的、各个部族的祖先结合为一个整体。无论是世代演化说,或五行之说,或炎、黄为弟兄说,或是古帝王征伐相代说,或黄帝为四代共祖之说,都是以“过去”来诠释当时华夏这个“想象群体”的历史述事(historical narratives)。无论是那一种诠释,黄帝都逐渐得到一个特殊的地位——在征服相代说中,他是主要的征服者;在五行说中,他居中制四方;在世代演化说中,他是由蒙昧到文明的转戾点。更不用说,在以黄帝为虞、夏、商、周共祖的历史建构中,他成为各代统治家族的血缘起点。
在此,有几点值得我们深思。首先,在近代中国国族建构中,中国知识分子曾以黄帝作国族之“始祖”、“战神”等隐喻;事实上,此种黄帝隐喻与想象早已出现在战国末至汉初的华夏社会上层之间。其次,以“黄帝后裔”或“炎黄子孙”为隐喻之近代中国国族想象,也是一个以“英雄祖先”为起始的族群线性历史想象。然而如前所述,此种以“英雄祖先”为起始的线性历史,最晚在战国晚至汉初时期也出现了。黄帝与历法或历法起始的关系,亦以黄帝隐喻一个线性、量化历史时间的起始。第三,学者常指出,在近代国族主义之下,知识分子一方面强调古老的文化传统与祖先起源,一方面强调国族之创新性,及其与过去之间的“断裂”。我同意这个看法,我也曾以“羌族妇女服饰”的例子,说明此种国族主义特色。然而由战国至汉初的黄帝论述中,“黄帝”一方面成为时代开创者,与文物之创造发明者;另一方面,他与炎帝及炎帝时代间有明显的对立与断裂。这些都可以让我们思考,是否某种类似“国族”之新认同,此时已出现在战国末至汉代之间的古代中国?当然,即使如此,它与今日之“中国国族”仍有相当差别。
西汉时司马迁所著的《史记》,其中有关黄帝之论述,综合了战国末以来华夏知识精英整合上古诸帝王的种种尝试。此文献之《五帝本纪》中称黄帝为少典之子,姓公孙,名轩辕。他生于神农氏之末世,曾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打败炎帝。又率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擒杀蚩尤,因而得代神农氏为天子。文中又称黄帝在得天下之后,“披山通道,未尝宁居”;他的征途,东至于海,西至空桐,南至于江,北逐荤粥。文中又提及,黄帝时之官名皆以云命,因称黄帝为云师,并记载黄帝封禅、获宝鼎、迎日推筴(制历)等事。该文又称黄帝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最后,“五帝本纪”记录黄帝之子孙——玄嚣、昌意为黄帝之子,颛顼为黄帝之孙,帝喾为黄帝曾孙,尧为帝喾之子,舜则是颛顼的七世孙。
我们可以从上述许多战国至汉初时期有关黄帝之论述中,找到《史记》这个有关黄帝之文献取材根源。然而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文本,它经过司马迁搜集裁剪资料、编排书写,成为一篇有社会功能与有目的之社会记忆,最后在某种社会与政治情境中被保存下来。而此种由选材、制造到使用、保存的过程中,都蕴含与表现作者在其时代与社会背景中的认同、区分与相关情感。以“选材”与“制造”来说,司马迁显然承继并发扬一个以英雄圣王为起始的线性历史,以结束一个乱世的征服者黄帝为此历史(时间)的起始,以英雄征程来描述英雄祖先所居的疆域(空间),以英雄之血胤后裔来凝聚一个认同群体(华夏)。在“使用”的层面上,此“黄帝”社会记忆之流传,强化一体的华夏认同(以及华夏与戎狄蛮夷之区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区分,以及两性之区分)。最后,司马迁所建构的“黄帝”记忆被后世华夏不断的回忆、重述与再制(再组合与再诠释),因此得到保存(以及相对的造成其它祖源记忆的废弃与失忆)。
由《史记》的其他篇章中,更能看出“黄帝”记忆在界定或凝聚“华夏”上的功能。如在三代帝王“本纪”中记载,夏禹是黄帝的玄孙,殷契之母是帝喾次妃,周始祖弃之母则是帝喾元妃。而黄帝及其子孙,包括夏、商、周三代王室及其支裔,又是东周华夏诸国王室的祖源。值得注意的是,东周时期在华夏政治地理边缘其民多为“蛮夷戎狄”的诸国,据《史记》记载,其国君也自称是黄帝之裔。如,对春秋时偏居东南的吴国,《史记》有如下记载:
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用,以避季历。季历果立,是为王季,而昌为文王。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自太伯作吴,五世而武王克殷。封其后为二:其一虞,在中国,其一吴,在蛮夷。
因此春秋末期的吴王自认为,也被当时的华夏认为,是姬姓之国。与吴相敌的越国,在《史记》中其国君则为“禹之苗裔,而夏后少康之庶子也”;因此也是黄帝之裔。对于西方被视为戎狄的秦人,《史记》对其王室之祖源也有如下记载:
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大业取少典之子,曰女华。女华生大费,与禹平水土……。舜赐姓嬴氏。大费生子二人:一曰大廉,实鸟俗氏;二曰若木,实费氏。其玄孙曰费昌,子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
如此说来,秦人算是黄帝后裔的姻亲,也曾辅佐黄帝的后裔。然而,如果这是秦人自我宣称的祖源,那么这样的祖源也可谓是一种选择性记忆——知有母不知有父,藉以与黄帝系上血缘关系。
关于南方曾被视为蛮夷之楚国,《史记》也将之系于黄帝后裔。其说如下:
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高阳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帝喾命曰祝融。……以其弟吴回为重黎后,复居火正,为祝融。吴回生陆终。陆终生子六人,坼剖而产焉。其长,一曰昆吾,二曰参胡,三曰彭祖,四曰会人,五曰曹姓,六曰季连,芈姓,楚其后也……。季连生附沮,附沮生穴熊。其后中微,或在中国,或在蛮夷,弗能纪其世。
北方之魏,《史记》中亦称其公室为毕公高之后。“毕公高与周同姓。武王之伐纣,而高封于毕,于是为毕姓。其后绝封,为庶人;或在中国,或在夷狄。”
在《史记》中这许多的“族源”记录中,有几点值得我们注意。第一,这些古部族起源述事的书写模式,似乎是在原来各部族的“族源”之前添加一个与黄帝相关的起源。《史记》有关吴、楚两国王族源流记载中,都有一些相当长的父子相承谱系记录;这些看来都较像是本土族源记忆,并与同一记载中之“起源”——与黄帝有关的族源书写——之间有断裂、不衔接的迹象。又如,不同于夏帝系之“父系祖源”书写,殷、周祖源在此是以“母为帝喾之妃”与黄帝产生联系;此应是在殷、周两族“母系祖源”的族源述事上,添加上了黄帝血缘记忆而成。商周与夏之王室族源述事模式差异,也显示三代“共祖”之说的虚构性。
第二,几乎是毫无例外的,各族群“起源”都始于一位“英雄祖先”。显然有些曾流传的“兄弟故事”,如炎、黄为兄弟之说,被司马氏放弃。有些则被纳于英雄祖先“历史”之中;如楚世家中所称的昆吾、参胡、彭祖等部族之祖为兄弟(陆终之子)之说,如秦世家中的鸟俗氏与费氏两部族祖先为兄弟之说。第三,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以上《史记》有关吴、秦、楚、魏之族源述事中,司马迁都解释说,其子孙或在中国,或在蛮夷、夷狄。如此便将这些原被华夏视为蛮夷戎狄的华夏边缘族群,藉由“黄帝子孙”而纳入华夏之内了。不仅如此,《史记》中如是之记载,更成为华夏与非华夏间一个开放的、模糊的边界,使得后世许多边缘之非华夏得以假借此记忆成为华夏。总而言之,司马迁不只是参考战国至汉初作者们的作品,来完成《史记》中有关“黄帝”的述事。更重要的是,承继自战国至汉初的“华夏”概念,引导及影响他有关黄帝“历史”的取材与书写;相应的,他有关黄帝的“历史”书写(再建构),更进一步定义与诠释了“华夏”概念。
最后,我们必须厘清这样的“华夏”认同之本质;黄帝论述仍是一个很好的线索与指标。简单的说,我们可以将战国至西汉之作者们(包括司马迁)当作人类学田野中的“土著”,看看“土著”们如何追溯其祖先,或他们认为谁是此共祖的后裔。以此而言,首先,显然此时黄帝的血液只流入三代、春秋战国以来许多的大小封国之邦君家族及其支裔之中,并以“姓”作为此血缘联系的符记。所以,战国至汉代虽然有“华夏”认同,然而此与今日“每一中国人皆为炎黄子孙”之认同概念仍有一大段距离。其次,在《史记》有关黄帝之历史述事,及以黄帝为祖源的各国历史述事中,“历史”不只诠释“血缘”,也诠释其政权与领土的合理性。因此可以说,在汉初时期,以黄帝记忆来界定与理解的“华夏”与“中国”其含义是相近的;都蕴含着血缘、政权与领域三者一体之隐喻(metaphor)。第三,如果我们以“黄帝记忆”的扩张来思考“华夏化”问题,那么由战国末到司马迁的时代,知识菁英们所关心的除了各封君家族外,似乎只是“华夏之域”或“华夏之国”而非“华夏之人”。也就是说,在吴、越、楚、秦等华夏边缘之地,黄帝血脉只及于各地统治家族;此祖源记忆中的政治权力与领域隐喻,强化或改变各国统治家族原有的对“地”与“人”的政治威权,如此其“地”自然被涵括在华夏之域中。在此域中之民最初并非透过“血脉”,而是受“教化”,逐渐由“蛮夷戎狄”而成为华夏。至于在华夏的核心地区,似乎在春秋战国时也非所有的民众皆有姓;至少在作为社会记忆的文献书写中,此时他们绝大多数是没有声音的人群,因此也无由与黄帝牵上血缘关系。
如此黄帝记忆所界定的“华夏”或“中国”之人,与今日以“炎黄子孙”所界定的“中国人”或“中华民族”,其间自然有相当距离;其距离主要是后者在两种“边缘”上的扩大。一是,在政治地理边缘上,今之“炎黄子孙”比汉代“黄帝之裔”之范围更向外推移。二是,在华夏域内的社会边缘上,今之“炎黄子孙”比汉代“黄帝之裔”之范围更往社会下层扩大。以下我将说明,这两种边缘的变化都不只是近代国族主义下的创造,而有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推动此两种边缘人群认同变化的主要途径,便是华夏边缘人群对黄帝的“攀附”。
在前节我曾提及,据《史记》记载,春秋时吴、越、楚、秦、魏等国统治家族的祖源皆与黄帝有关。吴、越、楚、秦在东周时常被中原华夏视为蛮夷;魏与戎翟可能也颇有渊源。若这些祖源记忆,在东周时期也是以上诸国王室或公室自我宣称的族源历史,那么可以说,在东周时已有华夏边缘族群直接或间接以攀附黄帝来成为华夏了。无论如何,《国语》是中原华夏之人的著作;我们在以上边缘诸国的铜器铭文或本土文献中,都很难找到溯及黄帝或颛顼、高阳等黄帝后裔的本土记忆。因此即使有如《国语》吴语中,吴国之君口口声声称华夏各国为“兄弟之国”,称周天子为“伯父”等等之记载,仍不足以充分证明在春秋时这些国家的统治家族已自称是黄帝之裔了。或者说,当时的中原华夏想象一些边缘强国为黄帝之裔,这也是一种“攀附”。此种“攀附”(华夏想象流落在外的祖先后裔),也引起边缘族群的“攀附”(非华夏想象或假借一个华夏祖先)。
华夏边缘人群对黄帝的攀附,更清楚的表现在汉晋时期“蜀人”的例子上。近年来喧腾的广汉三星堆文化,证明在相当于中原的商周时期或更早,蜀地已有相当昌盛的文明,与具相当规模的政治体。我在过去的著作中曾提及,广汉三星堆文化有一重要历史意义被许多学者们忽略了;由汉晋蜀人对本地的文献记忆看来,当时他们已遗忘了这文化所代表的本地古文明。接下来的问题便是:如何遗忘?为何遗忘?
西汉末,在蜀人扬雄所著的《蜀王本纪》中,便表达了当地人对古蜀君王的“失忆”。该文称:“蜀之先,称王者有蚕丛、柏濩、鱼凫、开明,是时人萌椎髻左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从开明已上至蚕丛,积三万四千岁。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名曰柏濩,后者名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颇随王化去。”在这段文字中,“椎髻左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是将本地的“过去”蛮荒化。作者称,“从开明已上至蚕丛,积三万四千岁”及“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是将本地的“过去”神话化。最后,“其民亦颇随王化去”之语,是直接切断当今(汉代)蜀人与这些古人间的联系。将本地之过去(历史)“蛮荒化”、“神话化”,并切断与本地过去人群之关系,这便是汉代蜀人遗忘“过去”的途径之一。
遗忘过去更积极的途径便是建立新的历史记忆。《史记》中称:“蜀之先,肇于人皇之际。黄帝与子昌意娶蜀山氏女,生帝喾,立,封其支庶于蜀。历虞、夏、商。周衰,先称王者蚕丛。”这是将“蚕丛”纳入一个“可信的”线性历史之中。这历史的起点,便是黄帝。约成书于战国至西汉的《世本》中也记载:“蜀之先,肇于人皇之际。无姓。相承云,黄帝后。”以此来说,蜀人在此时也自称为黄帝后裔了。
蜀人对黄帝的攀附,更间接透过黄帝后裔——“禹”。《蜀王本记》中称,“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生于石纽。”晋人常璩在《华阳国志》中也称,在蜀之广柔县,“郡西百里有石纽乡,禹所生也。”扬雄、常璩、谯周等,都是巴蜀之人。蜀人的本土感情及相关历史记忆,更表露在《三国志》秦宓之传记中。该文记载,秦宓为蜀郡广汉人;时广汉太守夏侯纂曾轻蔑的问宓及本地功曹古朴,当地士人比其它地域之士人如何。秦宓傲然答称:“禹生石纽,今之汶山郡是也。”《三国志》中有多处记载中原人士对蜀人之轻蔑,以及蜀人的本土自傲。这都显示,汉代魏晋时蜀地之人,在整个华夏中仍居于华夏之边缘。此种认同边缘危机,使得他们有意攀附黄帝、大禹来强调自己的华夏认同。
晋常璩所著的《华阳国志》,是目前所见最早且较全面的蜀人本土地方志著作。书名“华阳”即有居于华夏南方边缘之意。在这本书中,他述说蜀(与巴)的起源称:“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喾,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这是蜀地本土之人攀附黄帝祖先的明例。在本书《蜀志》之末,常璩对蜀地之赞词中称“故上圣则大禹生其乡,媾姻则黄帝婚其女”——更反映了在此时代的蜀人认同中,黄帝、大禹都是值得骄傲的历史记忆。然而,有趣的是,在《华阳国志》有关古“巴蜀人”起源的问题上,常璩又引述了另一个说法:
洛书曰:人皇始出,继地皇之后,兄弟九人分理九州岛为九囿,人皇居中州制八辅。华阳之壤,梁岷之域,是其一囿。囿中之国则巴蜀矣。
我曾以“历史心性”来解读以上数据。简单的说,蜀人常璩以两种历史心性来说明本地人的“起源”。一是在“弟兄故事”历史心性下,作者述说巴蜀、中州及其它地区的华夏都起源于几个“弟兄”;但承认“人皇居中州”,自己的祖先居于边缘(辅)之巴蜀。二是,在“英雄历史”之历史心性下,他将本地古帝王的起源溯自黄帝,但承认黄帝为正宗,蜀的帝王为黄帝“支庶”。两种文本述事所显示的情境(context)都是——当时在如常璩这样的蜀人之自我意识中,他们是居于“华夏边缘”或“中国边缘”的。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黄帝的后裔或是人皇的弟兄,巴蜀之人与中原华夏的血缘联系仍只限于巴蜀的统治家族——统治君王的血液来自黄帝(或人皇兄弟),其臣民仍透过“国”(空间)的华夏化而成为华夏。
在华北沿长城的山岳与平原相接带,是历史上华夏与“戎狄”之势力进退相持的地区。西汉时期,便有南匈奴与鲜卑、乌桓部族傍于塞边或进入塞内居住。西方的羌人,也在东汉时期几度大规模侵入关中地区;在中国以夷制夷的政策下,有些羌人部族也留居下来。汉晋之末,中国衰微,近于边塞的“五胡”更纷纷入居华北。这些近边的各非汉部族,特别是其上层豪酋由于和汉人常接触,因此也在文化与历史记忆上有些交流。过去许多学者皆注意此时期北方异族汉化,汉人胡化,或胡汉文化交流的问题;关注的焦点多为服饰、语言、习俗与姓的变更等客观文化变迁。我在过去的一篇文章中,曾以“假借一个祖先”与“找寻失落的祖先后裔”等历史记忆与失忆主观机制,探讨此一时期发生在北方华夏边缘的族群认同变迁。Patricia Ebrey 则注意到中国文献中此时许多非汉部族贵冑都有了“姓”,与常可溯及炎帝与黄帝的家族谱系记忆;她所论及的,也是历史记忆与汉人认同的关系。以下我将延续并深入讨论这些问题。
《史记》中称:“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晋书》中亦称鲜卑人慕容傀之家族族源为:“其先有熊氏之苗裔,世居北夷,邑于紫蒙之野,号曰东胡。”据此,这两支北亚游牧部族的祖先都出于黄帝。然而,我们不清楚这是华夏对异族族源的想象,或是部分匈奴与鲜卑家族自己宣称的祖源。《晋书》中又记载,鲜卑贵族慕容云的家族源始为:“祖父和,高句骊之支庶,自云高阳氏之苗裔,故以高为氏焉。”依此看来,这慕容家族是自称黄帝后裔的。赫连勃勃,为匈奴右贤王后裔,然而根据《晋书》,他曾对别人说:“朕大禹之后,世居幽朔。”魏晋时期有许多羌人在关中地区聚族而居,他们中的一些豪酋家族也攀附黄帝之裔为其祖源。如南安赤亭羌人,姚弋仲,据称是有虞氏之苗裔。一篇碑文,《隋钳耳君清德颂》,记载着关中羌人着姓钳耳家族的祖源为“本周王子晋之后,避地西戎,世为君长”——这也应是该家族自我宣称的祖源。另一关中羌人巨姓,党姓家族,根据《元和姓纂》,他们自称是夏后氏之后。无论是大禹之后、高阳氏之后、夏后氏之后、有虞氏之后,或一位周王子之后,在中国文献所蕴含之社会记忆中都是黄帝有熊氏之后裔。在上述部分例子中,可以确信有些汉晋时期中国北边的“五胡”曾攀附黄帝或黄帝子孙为其祖源。
黄帝族源记忆在华北各贵冑名门家族间流传;在如此情境下,统一北方的鲜卑拓跋氏也未能免俗。《魏书》记载,拓跋氏的祖先源流如下:
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其后世为君长,统幽都之北,广漠之野……。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其裔始均,入仕尧世,逐女魃于弱水之北,民赖其勤,帝舜嘉之,命为田祖。爰历三代,以及秦汉,獯鬻、猃狁、山戎、匈奴之属,累代残暴,作害中州,而始均之裔,不交南夏,是以载籍无闻焉。
这是一篇历史记忆的“再制造”作品。取材于过去历史记忆的“碎片”,如黄帝之裔或在中国或在蛮夷、黄帝土德、黄帝之裔“始均生北狄”等等;加上新的材料(大鲜卑山、托跋)揉合制造,以为新的政治或社会目的而“使用”——自称为黄帝后代,始均之裔。不仅如此,这段历史述事还强调北方獯鬻、猃狁、山戎、匈奴各族之残暴,与其对中国的危害;这是强调拓跋鲜卑与华夏有共同的“边缘”或异族意识(the sense of otherness)。最后并以“始均之裔,不交南夏,是以载籍无闻”,来强调载籍所见之“獯鬻、猃狁、山戎、匈奴之属”皆与拓跋鲜卑无关;也就是切断拓跋鲜卑与猃狁、山戎、匈奴等“北虏”的关连。然而,出于南朝士人之手的《南齐书》与《宋书》中,则不将拓跋鲜卑视为“黄帝子孙”而仍视之为“虏”。前者称之为“魏虏”,谓是匈奴种;后者则称之为“索头虏”,说是汉降于匈奴的将领李陵的后裔。相对而言,较晚出的《晋书》(成于初唐),较容易接受许多北方异族贵裔家族为黄帝子孙。其原因可能是,《晋书》原以收录野史传闻多而著称,或因此采集了许多“土著观点”的族源述事。更重要的背景或是,此时所谓的“五胡”早已融入华北汉人社会之中,他们中许多出自名门者甚至在唐代中国朝庭任职高官。在唐代的宰相之中,我们便可找到几位出于“华夏边缘”的黄帝子孙。
如《新唐书》之宰相世系表中有“乌氏”,“出自姬姓,黄帝之后,少昊氏以乌鸟名官,以世功命氏。齐有乌之余,裔孙世居北方,号乌洛侯,后徙张掖”。由较早的文献看来,乌洛侯为远居黑龙江流域的森林草原游牧部落,与黄帝似乎没有什么关联。《新唐书》中又称,武威李氏家族本来称安氏,也是出自姬姓:“黄帝生昌意,昌意次子安,居于西方,自号安息国……至抱玉赐姓李。”唐代安氏家族的《安忠碑》,文中自称该家族为“轩辕帝孙,降居弱水”;说明来自西域的此一家族,的确自称是黄帝子孙。另有鲜卑没鹿回部落大人的后裔,窦氏家族,也远溯家族族源至夏后氏。
《新唐书》中又称,著名宰相侯君集之“侯氏”,出自姒姓,为夏后氏之裔;另一说是他们出自姬姓,在东周时“子孙适于他国”。同一文献记载,后来他们随从北魏孝武帝西迁(公元534年),被赐姓“侯伏氏”及“贺吐氏”,最后又改回“侯氏”。然而《隋书》中记载,当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时,由于大多数鲜卑人不通华语,孝文帝曾命“侯伏”侯可悉陵以鲜卑语译孝经。显然早在魏孝文帝迁洛之时(公元494年),已有一相当华化的“侯伏”家族了。我们仍无法排除一个可能:这个家族是夏后氏之裔或姬姓子孙,他们一直徘徊于汉与非汉的边缘。但更合理的解释是,他们原来便是一鲜卑部族贵裔;后由于娴习经学,因而有能力及意愿以“祖源”来攀附黄帝,以成为黄帝子孙。
本文中我以探讨“黄帝后裔”为主,然而对于“炎帝后裔”也有必要略及一二。成于魏晋之时的《后汉书》中,曾提及“西羌”是姜姓之族,三苗的后裔,然而并未提及炎帝。无论是三苗或姜姓,都喻有“失败者”或“受逐放者”之意。前面我曾提及几个魏晋时自称黄帝后裔的“羌人”家族,似乎他们并不接受自己是“三苗”或“姜姓”后裔之说。《周书》记载鲜卑宇文氏之祖先由来为,“神农氏为黄帝所灭,子孙遯居朔野……世为大人”。《周书》虽为唐代所修,但北周沿袭中国王朝修史的传统,也曾命官修国史,以为后世修史者所本。由于为黄帝所灭之神农氏即指的是“炎帝”,因而根据此记载,北周王室有可能是自称炎帝后裔的。
出于契丹的辽,在中古时期也被视为鲜卑后裔,因此元代托克托所撰《辽史》之中采取《周书》之说,认为辽是炎帝之后。然而《辽史》中也提及耶律俨所主张的说法,称辽为轩辕之后;由于此说较晚出,所以《辽史》作者认为不可信。耶律俨本人为辽贵裔,又曾受命编辽之国史实录,因此他的说法可代表一种“土著观点”——显示进入中国的部分辽人,对于本族族源此时有一种典范的说法,那便是“黄帝后裔”。辽代修史的耶律俨,必然曾读到修于唐代的《周书》,也接触到“宇文鲜卑为炎帝后裔”之说;显然他刻意选择“黄帝”为攀附对象。无论如何,《辽史》解释辽为炎帝之后,有一段话称:“庖牺氏降,炎帝氏、黄帝氏子孙众多,王畿之封建有限,王政之布濩无穷,故君四方者,多二帝子孙,而自服土中者,本同出也。”这段文本在两方面值得我们注意。第一,它以“君四方者”皆同出炎、黄,来合理化或模糊化辽以外夷入主中国之事,而这是出于元代蒙古史学家主持编修的历史述事之中。第二,由此亦可见,自北朝、隋、唐以来,除攀附黄帝外,攀附炎帝的贵冑家族也不少。
出于女真的金人,对于攀附黄帝便不感兴趣了。《金史》中提及,曾有官员建议说,金朝之祖为高辛氏,是为黄帝之后,所以要为黄帝建庙。当时曾任国史之官的张行信驳斥其说;他称,按照金始祖实录记载,只说是本族来自高丽,并没有出于高辛氏的说法。最后,皇帝也同意他的看法。元朝入居中原的蒙古贵冑,至少透过中国正史及《蒙古黄金史纲》、《蒙古秘史》等文献来看,他们心目中的蒙古族源皆与黄帝无关。十七世纪入主中国的满洲女真,在他们典范的本土族源记忆《钦定满洲源流考》之中,其祖源也与炎帝、黄帝不相关。为何进入中国的金人、蒙古与满洲女真对于攀附炎黄不感兴趣,这是一个值得重视及待深入探讨的问题。
上一节所提及的,是华夏政治地理边缘的黄帝攀附。这里所谓华夏的「政治地理」边缘,在我们一般观念中似乎也就是汉与非汉的族群边缘。我不愿称之为“华夏族群边缘”乃因为,若我们称有共同祖源信念(common belief of origins)的人群共同体为一“族群”,那么由战国至明清,在华夏域内并非一直是所有人的祖先源流记忆都能与“黄帝子孙”血脉相接。而是,有此谱系记忆的人群有一个由上而下的扩张展延过程。这个变化的关键,也就是家族——有“姓”与族谱记忆的族群——在中国社会中的发展。
关于中国宗族或家族的发展,许多中西学者早有许多论述;他们多将之视为一种中国社会结构特色。将之视为一种社会结构,似乎暗示着中国人自古以来一直凝聚在一个个“家族”之下。这种看法忽略了,有姓与文字族谱记忆的家族群体之存在与广布,在中国有一个发展过程。殷墟卜辞常见“多生”一词,学者指出此为商代异姓贵族的泛称。由西周金文所见,当时有“女子称姓”的习俗,显示这些以婚姻为结盟手段的贵族都是有姓的。铭文中提及作器者之妻、女、母之姓,也就是作器者藉此夸耀本国、本家族的政治结盟关系。无论如何,这些称姓的都是贵族之家。西周中晚期的一些铜器铭文中,出现了“百姓”一词;如《兮甲盘》中的“诸侯百生”,《叔女弋簋》中有“百生朋友”,《善鼎》中的“宗人—与百姓”。这“百姓”应是国内或诸国间,许多不同姓之贵冑家族的泛称。到了春秋战国时,“姓”仍只是各地大小封君贵族及其后裔支庶的专利。许多先秦文献中都提及“百姓”,各种文本都显示这些“百姓”与其统治者间有密切的关系。甚至统治者是否能安于其位,都要看百姓是否奉服。因此,这些“百姓”约略与周之城邦时期“国人”所指涉之人群范畴相近,或为“国人”群体的后裔及延伸。由一些考古出土的文献或其它文字材料中,也可以知道当时中国底层社会之民很可能大多是没有姓的。
汉与魏晋南北朝时期,自称或被视为“黄帝子孙”的族群,有增加、扩大的趋势——有华夏域内之各朝帝裔与门阀世族,有以非华夏入居中国的君王及他们辖下的部族领袖与大姓家族。到了唐宋时期,由于科举盛行以来的社会流动,有姓并得以此溯及一个荣耀祖源的家族,在中国社会之中层里逐渐普遍;也就是,更多的士族之家也直接或间接的成为黄帝世冑。至清末民国初年,在中国社会之中、下阶层里,这样的人群单位便是无所不在了。家族或宗族族谱的功能之一,便是将一群人的“起源”连结在中国典范历史之轴在线。这条轴线的起点,便是黄帝;如此使得一个家族得以直接或间接与黄帝发生关联。由于在历史过程中得姓及相关谱系记忆的家族愈来愈普遍,因而由此成为黄帝子孙的人群单位,在华夏领域内也愈来愈多,且愈往社会中、下层扩张。
我们可以说,若古代华夏是一个“族群”,那么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中,构成此族群的因子是以“姓”为血缘符记,以可与中国线性历史述事联系之家族历史为集体记忆的各个家族。在中国,约自汉代以来,“百姓”代表被统治的众民即有此含意——受统治的是许多以姓为别的家族。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是:究竟从何时起,所有中国域内的民众都有了“姓”,或自何时起人们都有文字家族谱系历史。一位唐代的皇后曾问臣下说,当前许多士大夫谈起本家氏族,都说是“炎、黄之裔”,难道上古没有百姓吗?这位大臣,张说,答道:
古未有姓,若夷狄然。自炎帝之姜、黄帝之姬,始因所生地而为之姓。其后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黄帝二十五子,而得姓者十四;德同者姓同,德异者姓殊。其后或以官,或以国,或以王父之字,始为赐族,久乃为姓。降唐、虞,抵战国,姓族渐广。周衰,列国既灭,其民各以旧国为之氏,下及两汉,人皆有姓。
这段文字显示,一位唐代的中国士大夫根据当时的历史知识,曾认识到“姓族”有一个由上而下、由寡而众的社会发展过程。然而,他将此发展之历史过程定于黄帝时期至两汉之间,则起点与终点都未免过早。晚至唐代,在中国偏远与边陲的乡间可能还存在尚未有姓的民众。再者,由于相关的历史记忆模式有异,所谓“姓”,在中国域内不同地域、不同社会阶层的人民间有不同的族群认同意义(说明详后)。无论如何,以上唐代张说的话,也显示他认为有“姓”与否可作为华夏与夷狄之分野。宋代郑樵在所著《通志》中称:“三代之前姓氏分而为二,男子称氏,女子称姓。氏所以别贵贱;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今南方诸蛮此道犹存。”这段论述指出,上古时期在华夏之内只有上层贵族有姓氏,一般平民无姓氏。无论如何,以上数据显示唐宋时期的中国士大夫认为,当时所有的“百姓”都是有姓的;即使他们不见得对当时中国最边缘、底层民众有深入的了解。
即使我们相信到了唐代或更早所有的中国民间家庭都有了“姓”,但仅只有姓,与有姓并得以文字族谱溯及一个在历史上足以自傲的祖源,两者仍有相当差距。在中国偏远的乡间百姓间,有些口传的家族历史记忆至近代或至今仍是以“弟兄故事”为起始的历史来表述。我曾在川西北白草河流域的山村中,采录人们的口述家族历史。以下是两位老人家的说法:
(1)听我祖祖说,就是湖广填四川的时候…。当时是张、刘、王三姓人到小坝来。过来时是三弟兄。当时喊察詹的爷爷就说,你坐在那儿吧。当时三弟兄就不可能通婚,所以就改了姓。刘、王、龙,改成龙,就是三条沟。一个沟就是衫树林,那是刘家。另一个是内外沟,当时是龙家。其次一个就争议比较大,现在说是王家。这三个沟,所以现在说刘、王、龙不通亲。三兄弟过来的…。
(2)我们是湖广孝感过来的,五兄弟过来,五个都姓王。主要在漩坪、金凤、白泥、小坝。这五个兄弟,两个到小坝;一个在团结上寨,一个在这里。
我们可以看出,如此的“家族源流”记忆是以祖先的弟兄关系来合理化当前的族群关系(如例一中,三条沟的村民),或表现期望与想象中的族群关系(如例二,小坝与邻近三个乡的王姓家族);两者的重点都在于当前的“本地情境”(local context)。此与一般中国文字族谱中——在“英雄祖先”历史心性之下——以一个英雄祖先为起源,以线性家族历史来区分主流、分支之书写有相当差别。前者以“弟兄”隐喻,强调一种平等、合作与对抗的族群关系。后者以“英雄圣王”隐喻,强调贵贱、嫡庶、长幼间的社会阶序。前者是一种结构性的历史,反映一家族在本地社会族群结构中实际或期望中的地位。后者是一种线性历史,且是线性中国历史述事的一个小分支,因此反映一家族与外在社会的联结,及其在整体中国社会中实际的或宣称的优越地位。严格的说,只有后者构建作为“炎黄子孙”的中国人或汉人;前者则表现此群体中许多边缘人群的历史心性。
由现存一些清代家谱序言看来,“修谱”对于中国乡间百姓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若非是数世积德累业,出几位入学得有功名的弟子,不得及此。因此,许多家族皆有姓,并得以溯及一个足以自傲的祖源,在中国民间社会中必然有一渐进过程。此渐进过程,与中国社会的“民间化”,以及一些历史记忆与文化习俗、符号与价值,透过口述与文字流布逐渐往社会中下层普及,是密切相关的。虽然我们无法得知“姓”以及相关族源记忆,透过文献、口述与图像在中国社会中全面的流布与演变。但文献记忆中的家族“系谱”,可作为一项很好的指标。也就是说,当某一族群的“祖先系谱”出现在中国文献传统中并得以保存留传下来时,其意义在于该族群透过“我族历史”宣称一种自我认知(self-awareness)与认同(identity);此种自我认知与认同,也得到当时主体社会的注意与认知。
以此而言,黄帝作为“百姓”之共同祖源,有其起始优势。虽然中国先秦文献中多处提及“姓”,但最详细的记载见于《国语》有关黄帝后裔的描述:
同姓为兄弟。黄帝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唯青阳与夷鼓皆为己姓。青阳,方雷氏之甥也;夷鼓,彤鱼氏之甥也。其同生而异姓者,四母之子别为十二姓。凡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姞、儇、依是也。唯青阳与苍林氏同于黄帝,故皆为姬姓。同德之难也如是。
许多学者都曾在“史实”层面讨论这篇文献。但我们若由社会历史记忆的角度来看,更重要的是这文献提及许多的“姓”都出于黄帝后裔,因此它使得“黄帝之裔”更容易被后世之“百姓”借用与攀附。如前引文中,唐代的张说把各家族有“姓”的由来,推溯自黄帝二十五子,便是一个例子。南宋罗泌在其所著《路史》之中亦言,太史公(司马迁)以黄帝为记史之首,原因之一是以为后世氏姓无不出于黄帝。
文献系谱也就是“氏姓之书”;对此《隋书》作者曾溯其历史,称:
氏姓之书,其所由来远矣……。周家小史定系世,辨昭穆,则亦史之职也。秦兼天下,戋除旧迹,公侯子孙,失其本系。汉初,得《世本》,叙黄帝已来祖世所出。而汉又有《帝王年谱》,后汉有《邓氏官谱》。晋世,挚虞作《族姓昭穆记》十卷。齐、梁之间,其书转广。后魏迁洛,有八氏十姓,咸出帝族。又有三十六族,则诸国之从魏者;九十二姓,世为部落大人者,并为河南洛阳人。其中国士人,则第其门阀,有四海大姓、郡姓、州姓、县姓。及周太祖入关,诸姓子孙有功者,并令为其宗长,仍撰谱录,纪其所承,又以关内诸州,为其本望。
在司马迁作《史记》时,《世本》便是他重要参考文献之一。这《世本》,据班固之言,“录黄帝以来至春秋时,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因此,这是帝王公侯等政治领导家族的系谱。晋人皇甫谧所作之《帝王世纪》,更不用说,记载的也是帝王家谱。汉晋时的《邓氏官谱》与《族姓昭穆记》虽失传,但由书名看来,是记载一家或诸家门阀世族系谱之书。由《隋书》所载的氏姓之书来看,有帝王系谱,有以一地为主的诸姓谱,有以一姓氏为主的系谱,更有多种名为“百家谱”的系谱书。这些祖先源流见于记载的“家族”,除帝王世家外,应即为《隋书》中所称的郡姓、州姓、四海大姓等等。因此可以说,到了隋唐时代,有文献系谱记忆的“家族”,比起战国至汉初时期增加不少。唐代修谱之风更盛,此时各著名系谱之书,如《氏族志》、《姓氏录》等,多为官方所修。学者认为,这是随着新政治势力而起的新兴家族,借着官方力量的介入与支持,由修谱来重新评定氏族高下,以建立一个由皇室为中心的氏族集团。唐代官修的《氏族志》中,录有293姓,共1651家,无论如何,这仍只是当时中国域内民众人口金字塔的最上层。
至于这些“家族”的祖源,《新唐书》中对于曾有子弟任官宰相之家族有简单的祖源介绍,因此可以显示其大要。在此文献中,这些无论出身是汉或非汉的唐代宰相,其家族源始多直接或间接与黄帝有关,另有一些则与炎帝相关。譬如,张氏,“出自姬姓.黄帝子少昊青阳氏子挥为弓正,始制弓矢,子孙赐姓张氏。”任姓,“出自黄帝少子禹阳封于任,因以为姓。”又如,薛氏,“出自任姓。黄帝孙颛顼少子阳封于任,十二世孙奚仲为夏车正,禹封为薛侯。”傅氏,“出自姬姓;黄帝裔孙大由封于傅邑,因以为氏。”又如,周氏,“周氏出自姬姓;黄帝裔孙后稷”,后稷为周人始祖。又如,吉氏,“吉氏出自姞姓;黄帝裔孙伯儵封于南燕,赐姓曰姞。”祝氏,“出自姬姓;周武王克商,封黄帝之后于祝。”董氏,“出自姬姓;黄帝裔孙有飂叔安,生董父,舜赐姓董氏。”以上皆为在唐代为相,或累世子弟多人为相的“黄帝子孙”。唐代世家中的“炎帝子孙”亦不少。在《新唐书》中有封氏,“出自姜姓,炎帝裔孙巨为黄帝师,胙土命氏,至夏后氏之世,封父列为诸侯,其地汴州封丘有封父亭,即封父所都。”又有宇文氏,根据此文献其来源为:“神农氏为黄帝所灭,子孙遁居北方。鲜卑俗呼草为俟汾,以神农有尝草之功,因自号俟汾氏,其后音讹遂为宇文氏。”这只是部分直接攀附黄帝(与炎帝)的例子;其他如以姬周之王子,或汉之刘姓宗室为祖源的家族,间接的也成为黄帝之后了。前面我曾提及一位唐代皇后的疑问——为何这些士大夫家族都说是炎、黄之后——这也证明,唐代士族攀附黄帝(与炎帝)是相当普遍的。
许多研究中国族谱的学者皆认为,宋代是中国系谱书写史上一个变化关键年代。唐代官修的谱系,大多在战乱中散失。重新崛起的家族修谱之风,转入民间私家士人之手而更见昌盛。魏晋至唐不但许多谱系之书是由官修,即使民间修纂者也必须上之官府,这是由于在此时期任官必需先问家世门第。但在宋代之后,任官不再“稽其谱状”,因而家族系谱书写也与官府脱了关系。脱离政治威权的干涉,由此下至明清时期,各家族私家修谱之风大盛。到了清末民初,研究者认为已到了“姓姓有谱、家家有谱、族族有谱”了;或者,据估计从清代到二十世纪中叶,在中国各地所修之族谱不下两万种。可以说,宋代以来中国有家谱的“家族”仍持续,或以更快的速度,往中国社会的边缘底层社会下移。
宋代以后的私修家谱,其中有一个重要成分便是“宗族源流”或“姓氏源流”。在这一部分,许多家族便与“黄帝后裔”直接或间接的牵上了血缘关系。但大多数的例子,被攀附的不是“黄帝”而是一个历史上的名人贵冑。然而,由于在汉代司马迁所作《史记》中,夏商周三代宗室皆黄帝之裔,东周列国王室之祖皆出于炎黄之后,唐代《氏族谱》中各名门士族也大都自称是炎黄后裔,因此明清各家族之“宗族源流”很难不与黄帝、炎帝发生关系。特别是,明清时期学者仍热衷于修纂统合万宗的“姓氏书”;如清初顾炎武在其《日知录》中所言:
愚尝欲以经传诸书次之。首列黄帝之子,得姓者十二人。次则三代以上之得国受氏,而后人因以为姓者。次则战国以下之见于传记,而今人通谓之姓者。次则三国南北朝以下之见于史者。又次则代北复姓辽金元姓之见于史者。而无所考者,别为一帙……。此则若网之在纲,有条而不紊,而望族五音之纷纷者,皆无所用,岂非反本类族之一大事哉?
如此始于黄帝之“姓氏书”,自然将当时绝大多数的中国家族都纳入黄帝家族之内了。事实上,明代有官修的《万姓统谱》,序言中称:“夫天下,家积也;谱可联家矣,则联天下为一家者,盍以天下之姓谱之”;此已明确表示以统谱“联天下为一家”的企图。而此万姓一家之起始,此序言也将之归于黄帝。明末清初曾积极反满,后来遁入乡间隐居著述的王夫之,曾着《黄书》以发扬民族之义。此书之书名,即有以黄帝为汉族认同符记之意。其书后序中称,“述古继天而王者,本轩辕之治,建黄中,拒间气殊类之灾”;更明白表述一个以黄帝为起始,以非我族类为边缘的汉族族群想象。然而在同书中他也表示,许多住在帐幕中随畜迁徙的,与住在边疆与汉人风俗有异的人群,其祖源都是出于少数几个姓。虽未言明,他所谓“数姓之胤冑”,主要应指的是“炎、黄后裔”。以此看来,以王夫之这样的汉族中心主义者,在相关历史记忆的影响下,也曾将“炎黄子孙”之想象扩及到华夏域外“殊俗”之地。
族谱或家谱,是一个血缘群体的“历史”。以文字书写形式出现的“文献系谱”,代表一“族群”以此强力宣告本群体的存在,并宣告其与中国整体社会的关系。此文献之保存与流传,使得此种宣告易为主体社会认知。因此有“文献系谱”的家族在中国由上而下、由寡而众的发展,其意义是:在“中国”此一领域内,得以发声且被认知并能与“炎黄子孙”血脉相联的“族群”,自战国以来由寡而众、由上层而下层逐渐浮现——愈来愈多的社会下层族群单位(家族)得以宣称自己存在,其存在也被主流社会所认知。这些“族群”,也就是构成更大的“族群”——华夏或中国人——的次群体单位。所以一个魏晋时人所称的“百姓”,唐宋时人所称的“百姓”,以及二十世纪以来人们所称的“百姓”,在社会阶层范踌上都应有些区别。
在前面,我提到两种“华夏边缘”人群攀附黄帝为其祖源的历程。此种人们攀附黄帝的情感丛结,很早即表露于一则有关黄帝的传说上。在许多中国早期文献中都可发现此传说或其遗痕。如《史记》记载称:
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须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宫从上者七十余人,龙乃上去。余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龙须,龙须拔,坠黄帝之弓。百姓仰望,黄帝既上天,乃抱其弓与龙须号。
在《楚辞》中亦有“轩辕不可攀援兮,吾将从王乔而娱戏”之语。直至今日,这故事还常出现在一些名为“中国民间故事”之图书中;亦可见此神话传说流传之深远。这神话故事之出现及被一再重述(再现),都显示其文本中一些人、事、物,在中国社会中有重要之象征意义。这些历史与文化象征意义,也不断被人们作选择性的认知与诠释。其中,“黄帝”与“鼎”皆象征着政治权力;黄帝在铸鼎成功后乘龙升天,代表政治上的最高功业成就。鼎、后宫、小臣也代表荣华富贵,拥有鼎与众多后宫、小臣的黄帝乘龙升天,也象征得富贵之极。鼎也是炼丹工具,如此黄帝在铸鼎后升天,象征透过道术、医药所得之超脱生死。后来在中国民间传说中,特别在道教传统中,黄帝成为修练成仙的符记;一个平民也可能藉修练、吞丹而羽化成仙,这可能显示民间一种攀附皇帝的期望。无论如何,小臣们攀龙须希望与黄帝一同升天,是这神话中最重要的一项象征主题——攀附——无论是追求权力、富贵或健康永生,黄帝都成为人们攀附的对象。
攀附,产生于一种模仿欲望,希望藉由模仿而获得某种身分、利益与保障。众人攀附的对象,自然被认为在政治、社会与文化上有卓越的地位。许多中国学者在讨论“汉化”过程时,便因此抱持着一种族群中心主义(ethno-centralism)想象——中国文化是优越的,因此受到边疆异族的学习、模仿。然而这只能说是部分事实。另一部分事实是,文化与认同的攀附欲望,产生于攀附者与被攀附者间的社会与文化差距。华夏与“华夏边缘”间此社会与文化差距,不一定是客观事实;有时或由于中国在政治上对“边缘”地区的征服、统治,或由于“汉人”对边缘“土著”与“土著文化”的歧视,以及相随的,“汉人”以自身文化向“边缘人群”所作的夸耀。在此,我所称的“土著文化”与“边缘人群”,包括政治地理边缘或域外的“异族”人群,也包括中国域内社会边缘的“乡野”人群。
对他者文化与历史的歧视,及以自身文化与历史所作的夸耀,造成人群间的“区分”;此略等于 Pierre Bourdieu 所称,以品味高下之辨所造成的社会区分(distinction)。在本文的例子中,受品评的不是“品味”而是“起源历史”。许多华夏家族夸耀自身的优越祖源,并嘲弄或想象他者较低劣的祖源;如此区分孰为核心、孰为边缘,孰为主体、孰为分枝,或孰为征服统治者后裔、孰为被征服者或受统治者之后裔。在此情境下,常造成边缘之政治或文化弱势者的攀附动机。此攀附动机,相当于研究人群信仰与暴力根源之 René Girard 所称的模仿欲望(mimeticdesire)。在本文的例子中,受模仿、攀附的也是一个“起源历史”;而当模仿、攀附者在宣称一个足以荣耀的祖源时,也同时在对他人作一种夸耀。如,魏晋南北朝至辽金时期,进入中国的北方各部族领袖家族,常以攀附黄帝或炎帝来合理化自身的统治者身分,并以此夸耀并自别于其他北方部族。又如唐宋以来许多中国域内之新兴士族家庭,由建构一个家族历史而直接或间接攀附黄帝,以此夸耀并自别于其他家族。
Pierre Bourdieu 所称以评价品味所造成的社会区分,以及 RenéGirard 所称的模仿欲望,皆发生在社会中彼此亲近或常有接触的群体之间。的确,文化与历史的歧视、夸耀与攀附,也并非经常发生在文化、族群、地理与社会距离遥远的群体(如华夏与非华夏、士族与乡民)之间。相反的,它们常发生在较亲近的群体之间,而形成一连串相互歧视、夸耀与攀附的炼状反应。此种社会文化过程发生的本地情境(local context),在有限的文献记载中不易呈现,或经常被扭曲。概念上“样版化”(范准化)的偏见,使我们在探讨各种认同变迁或社会流动时,常注意由“非汉人”到“汉人”的转变,或“平民”如何跻身“士族”。事实上,模仿与攀附发生的本地情境经常是文化、社会界线相当模糊的亲近群体间之互动。界线模糊,使得一方有认同危机,因而以夸耀来造成或强调区分。另一方则因不堪受歧视,或在文化夸耀的熏染下,接受一种文化与历史价值观(什么是高尚的文化,什么是高贵的祖先源流)而爱慕、欣赏夸耀者之文化,因而以模仿、攀附来改变族群界线。
我曾以近代川西北湔江上游的“青片、白草土著”为例,说明如此的本地情境。北川之白草、青片住民,在中国文献中常被称为“羌人”或“羌番”。明代受中国征服统治后,汉人移民以及他们带来的汉文化、历史记忆与认同逐渐深入白草、青片河上游村寨间。在清末与民国时期,在此形成一个模糊的汉与非汉边缘;大家都认为自己是汉人,却认为上游村寨人群都是蛮子。透过一端(自称汉人者)文化符号与历史记忆的展示与夸耀,以及另一端(被视为蛮子者)的模仿与攀附,明清以来愈来愈多的北川人自称为“汉人”。他们除了强调本家族为来自“湖广”之某姓家族外,都以祭拜大禹来攀附汉人认同。然而,自称“汉人”并辱骂与嘲弄上游“蛮子”的人群,仍被下游的或城镇的人视为“蛮子”。当地老年人说,过去骂“蛮子”,事实上是“一截骂一截”。相反的,我们可以说,自称汉人的则是“一截攀一截”——这便是我所称,炼状的歧视与攀附连带反应。这样的族群认同本地情境,以及相关历史记忆与文化符号的展演与操弄,便是一种“汉化”或族群边界变迁的进行机制与过程。
清末民国时期北川青片河、白草河流域之族群体系,可代表汉人——或更大范围的中国民族——起源与形成过程中某一个阶段现象。与此同时,或至少从清代中叶以来,其西邻岷江上游村寨人群间的一些族群现象则可代表此过程中一个较早阶段。在此(茂县),一般村寨民众并不自称汉人;他们自称“尔玛”,但被上游村寨人群视为“汉人”,被下游村寨人群视为“蛮子”。然而他们的土司与头人家族,却常自称其祖先来自汉地。如道光《茂州志》称当地五个土百户(土著首领)的祖先都来自汉区;大姓、小姓、大姓黑水、小姓黑水四土官家族的祖籍都是“湖广”,松坪土官的祖籍则是陜西。又如汶川的瓦寺土司索姓(或姓桑朗)家族,其祖先为嘉绒头人,在明代受中国之邀来此平乱而留居,世代源流有族谱可稽。即使如此,在一九二○年代,土司自家人曾告诉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调查者黎光明等人,谓本家族为汉人移民后裔,称“河南人有桑国泰者,在张献忠剿四川以后带了四个儿子到四川做移民……。四子桑鹏,便来此刻的汶川,到土司家里承袭了土司职”云云。黎光明在与一个瓦寺家土官的谈话里,也曾注意一个有趣的现象:
他的谈话中每每有“他们土民”、“我们索家”的话头,其意思是不承认索家是土民的同种。他睡在鸦片烟灯的旁边,替我们谈“他们土民的老规矩”。
在此,头人们攀附汉人祖源,模仿汉人乡绅习俗,并以此向邻人(本寨子民或上游村寨人群)夸耀。他们嘲弄、歧视这些邻近人群,但同时他们也被邻近之下游人群及外来汉人歧视。村寨百姓模仿、攀附下游“汉人”或本地头人家族的文化习俗(包括汉姓与溯及汉人祖先的家族历史),并以此夸耀以自别于上游的“蛮子”或本寨其它家族。
以上所述清代以来北川与茂县的族群体系与相关族群现象,具体而微的反映了数千年来曾发生在许多华夏边缘地区的族群认同变迁过程——居于华夏边缘的土著头人家族,模仿、攀附近于汉文化之邻近人群所夸耀的汉文化与汉人祖源,并以此向较远离汉文化的其子民与邻近族群展示、夸耀。居于华夏边缘的一般民众,则模仿、攀附邻近汉人或本地贵冑的汉文化习俗与汉人祖源。如此一截一截邻近群体间相互的夸耀、歧视与模仿、攀附,推动华夏边缘的扩张。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攀附不只是单向的“边缘”向“核心”华夏的模仿;有时亦有华夏或汉人攀附、假借外来族群的文化与历史。在北朝时,如《颜氏家训》所载,有北齐士大夫以教子习鲜卑语与弹琵琶为荣,这便是一种华夏士族对外来统治者的文化攀附。如,在清末至民国初期,接受“黄帝为西来巴比伦酋长”之说的中国知识分子,也是在受西方文明(含历史)夸耀之影响下,所作的祖源历史攀附。又如,刚才提及的北川青片、白草地区的“汉人”,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透过文化符号与历史记忆的展示夸耀与相对的模仿攀附,愈来愈多的人成为羌族。在他们新的祖源建构中,炎帝为所有羌族的祖先;他们认为,炎帝与黄帝的弟兄,因此羌族也是古老的华夏,也是古老羌族“大禹”的后裔。
在本文中,我说明近代以“黄帝”或“炎黄”为共同起源想象的中国国族建构,乃承自于一古代历史与历史记忆基础。也就是说,近代“中国国族”建构,是一沿续性历史过程的最新阶段。在这历史过程中,华夏或中国之人这样的“我族”认同,在祖源“黄帝”中已蕴含领域、政治权力与血缘之多重隐喻。这样一个浑沌初成的族体,在战国时代以来,透过攀附“黄帝”或炎帝与炎、黄后裔,逐渐在两种“华夏边缘”扩张——政治地理的华夏边缘,以及社会性的华夏边缘。也就是说,透过“姓”以及与姓相链接的祖源历史记忆,可以与“黄帝”(或炎黄)直接或间接发生血缘联系的“族群”逐渐往中国周边,以及中国域内之社会下层推移。
在“华夏”的政治地理边缘方面,许多本土社会的领袖家族或知识菁英,由攀附黄帝而跻身华夏之内,同时也将本地纳入华夏之域。由战国至汉晋时期,这样的过程发生在吴、越、楚、赵、魏、秦、滇与巴蜀等地。华夏之“域”的边缘至此已大致底定,此后只有局部的变化。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五胡”,事实上是原居此域内或由外进入此域内,而自称黄帝或炎帝之裔的族群。唐、宋时期的北方士族中一些原出于西域或草原的家族,也在长期定居中国后才攀附炎黄为祖源。更值得注意的是,由中古时期开始,一些进入中国的北方部族如女真、蒙古等以及西方的吐蕃,较少攀附炎、黄为其祖源。因此直至今日,以“黄帝之裔”或“炎黄子孙”为隐喻建构之“中华民族”或“中国民族”,难以涵括汉族之外(或传统华夏之域以外)的各北方、西方“中国境内少数民族”。也因此,强调“炎黄子孙”的中国国族概念难以得到满、蒙、藏等民族的普遍认同。在传统华夏之域的南方或西南部分地区,则情况有些不同。
在本文中,我并未论及华夏南方与西南边缘的情况。由许多文献中我们知道,历史上由得姓与得到一家族历史而攀附炎、黄的群体,一直在中国南方与西南边缘部分非汉族群中扩大蔓延。在此,经常上层领导家族有“姓“并自称是汉人,而一般百姓则无汉姓,或有汉姓但缺乏可与中国主流历史相联系的家族历史记忆。因此本文所提及的两个华夏边缘——政治地理的与社会性的——在此交迭,并形成一个模糊的华夏边缘。唐代《通典》中记载:”松外诸蛮……有数十姓,以杨、李、赵、董为名家,各据山川不相属役,自云其先本汉人。”宋代《通志》中称古时中国贵者有姓氏,贱者无姓氏,“今南方诸蛮此道犹存”——或也反映作者知道在“南方诸蛮”中,许多贵冑家族是有汉式之姓的。到了明清时期,在今日许多西南民族如羌族、苗族、瑶族、土家、畬族、白族、壮族等之地区,都有些土司或大姓家族宣称其祖源为汉人。在清代文献资料中,云贵地区的土司多“南京籍”,四川土司多“湖广籍”,皆反映此现象。他们甚至可以借着家谱中之“姓氏源流”,直接或间接与炎、黄之血脉相通。如厦门大学人类学博物馆中有一幅清代畬人家族祖图,此图首页之图象与文字便将此家族起源溯自“黄帝”。又如,修于一九四五年的湖北鄂西土家族《向氏族谱》中有“粤我向氏,系出汤王”之语,也可说是自我宣称为黄帝之后。同地之土家田姓家族,自称“田世雁门,系出有熊,黄帝之苗裔也”。子孙广布于湖南、湖北、四川、贵州诸省少数民族地区的南方满姓家族,其修于明末之族谱也称“粤稽我族发源于虞舜”。
在社会性的华夏边缘上,更活跃的祖源攀附在“华夏之域”内进行。然而由于“历史”只注意上层统治者与贵冑家族的“起源”,所以在社会中下层所进行的“炎黄子孙”攀附过程常被忽略。无论如何,族谱中的“姓氏源流”或“先世考”是一群体自我宣称的祖源。以此而言,中国家族与族谱书写的发展历史可解读为:藉此记忆建构与书写,可与“黄帝”或“炎黄”血脉相通的“族群”单位——有文字族谱记忆的家族——愈来愈多、愈来愈小,也愈来愈普及于中国社会的中下层。最后在此历史记忆与历史事实基础上,在国族主义蕴含的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精神上,晚清民初中国知识分子终于将黄帝与“每一个”中国人系上想象的血缘关系。
一九九五年以来,我曾利用多个寒暑期,在川西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作田野考察。在理县蒲溪沟的一个王姓羌族家中,我曾抄录一本该家族的家谱。此家谱修成于清代中叶。谱中记载:“我王氏之受姓也,始于周灵王太子晋。废居山西平阳,子孙世号王家,因以为氏焉。”由唐代之《元和姓纂》到明代之《万姓统谱》中,皆有记载王姓为周灵王太子晋之后;可见这个族源记忆的传承,也显示《姓氏书》之类的著作在统合族源记忆上的力量。然而在口述历史记忆中,本地王姓分为五大房,据称是由湖广来的五个兄弟分家所造成的。又有一种说法是,本地最大的三个寨子其住民来源为:从前有三个弟兄分家,以射箭来分地盘,箭射到不同的地方,于是这三个弟兄就分别在三个地方立寨。这个蒲溪沟中的王姓家族,居于本文所称华夏政治地理边缘,也居于华夏社会边缘。由于汉与非汉间之界线在此是模糊与变动的,此两种边缘并没有严格的划分。这个例子或许也表现汉人或中国人形成之普遍族群过程的一个缩影。在以“弟兄故事”为主轴的家族口述历史中,“过去”只诠释当前本地的族群关系;以“姓”为本的文字族谱记忆,则将本家族之历史与中国大历史述事接轨,也因此将一个家族与整个中华民族系在一起。于是在国族化或中国民族形成之历史过程中,口述传统中的本地“弟兄故事”族源历史,如流传古华夏间的“炎黄为弟兄”故事、古蜀人曾相信的“人皇兄弟九人”故事,以及本文所提及的北川白草河与理县蒲溪沟等地的“弟兄故事”一样,都逐渐在社会记忆中消失或被认为是神话传说了。
无论如何,在此“黄帝攀附”的长程历史中,“近代”的确是一个有重大变迁的时代。攀附黄帝的单位非“人群”而是“个人”;攀附不再是间接,而是直接(使每一个人成为黄帝子孙);知识分子、国家与媒体,也在新变局中得到前所未有的知识掌控与扩展能力,以推动黄帝攀附。以此而言,国族近代建构论者所言不虚。即使如此,无论是“黄帝后裔”或“炎黄子孙”之国族建构概念,都难以合理的将目前中华民族中北方、西方之满、蒙、藏,以及部分西南地区之少数民族,包括在此一血缘想象群体之中。因此在某种程度上,“黄帝攀附”代表由华夏蜕变为中华民族过程中沿续的一面;“近代中国国族建构”中最重要的想象、创新,与因此造成的“近现代”与“过去”之间的断裂,应是由于新的语言学、体质学、民族学与考古学对国族建构之影响。它们不一定使得“民族”分类与“国族”溯源更正确,但的确,它们使得国家或国族建构(包含黄帝攀附)有了更多可选择的诠释工具,因而造成中国(或华夏)之国族边缘变化。传统上王化之外的,或汉与非汉区分模糊的边疆(frontiers),变为国家边界内的边缘(peripheries)。因此,虽然对绝大多数的满、蒙、藏等边裔族群而言,黄帝或炎黄子孙历史记忆之意义不大。然而“蒙古人种”、“汉藏语系”与“仰韶文化”、“红山文化”、“北方青铜器文化”等等体质学、语言学、考古学范畴之建构、想象,与它们彼此间的联系,广泛被用以建立国族边缘与强化国族内部凝聚。
我们不能忽略,“黄帝”成为族源论述的焦点,除了在“近代”之外,还出现在战国末至汉初。因此在探讨“中国人”的形成与变迁时,“战国末至汉初”与“近代”似乎是两个重要的关键时代。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重要关键时代,也就是《史记》的出现,与《史记》首其端之“正史”书写传统结束(或历史研究与书写发生重大转变)的时代。《史记》不仅总结战国末至汉初以来的黄帝论述,它也创造了一个以“英雄祖先”为骨干(英雄传记与帝王世系)的“文类”(genre),所谓“正史”,并将“历史”与司马迁所称“其言不雅驯”之神话传说分离。此种纪传体之正史书写文类,至清末而消解;中国历史书写从此有了新的“理性”与新的结构。因此,研究“中国人”的本质及其变迁时,我们不仅可从“文本”分析相关情境,各种“文类”如正史、方志、族谱、异域游记及近代“民族史”的出现及其形式之改变,以及“历史”与“神话传说”分野之始与其间之界线变迁,都反映“中国人”之形成与转变过程中的一些本质变化;这些方面,值得再深入探索。
最后,在分析“黄帝后裔”或“炎黄子孙”时,我们的焦点常只在于“国族”、“民族”认同,与相关的华夷或中国民族与外族之分;被忽略的是,隐藏于这些“血缘论述”之后的人类性别、阶级间的核心与边缘区分。无论是由“英雄祖先历史”或“弟兄故事”来建构一群人的血缘联系,经常都是部分人的“起源”——统治者的血胤或男人的血胤——诠释了整个族群的“起源”。因此人们常透过新的“英雄祖先历史”或“弟兄故事”建构(女性与社会弱势者也常参与此建构),来改变可分享共同资源的“族群”之边界。然而在新的认同体系中,女性与社会弱势者的边缘地位经常没有多少改变。这也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马拉圭龙:南美超巨型恐龙(长25米/能与蓝鲸相比)
马拉圭龙是一种蜥脚下目中的泰坦巨龙类恐龙,诞生于8900万年前的白垩纪末期,体长普遍可以达到25米,属于巨型植食性恐龙的一种。首批马拉圭龙化石是在南美洲的阿根廷发现的,相对比较完整,其中包含了尾椎、肋骨以及四肢骨骼等。马拉圭龙的体型我要新鲜事2023-05-09 19:58:370000阿姬曼·芭奴还原图 阿姬曼芭奴长相如何是什么样的人
阿姬曼芭奴是古印度莫卧儿地区沙贾汗的爱妃,当人们将这位美丽的爱妃进行还原的时候,竟然发现这个女子可谓当时最美的女人。阿姬曼芭奴有着一对俊俏的双眼皮,眼睛炯炯有神,高高的鼻梁,笑起来还带着两个酒窝,戴着一顶高高的皇冠帽子,显得地位十分高贵,一张小小的瓜子脸引来了沙贾汗的无限喜爱,这就是最美丽的莫卧儿皇妃姬曼芭奴。一、阿姬曼芭奴和沙贾汗的感情怎么样我要新鲜事2023-05-08 00:42:2700010史念海:汉唐长安城与生态环境
中国历史上建都年代最长久的城市当数到长安。长安作为都城竟长达千有余年。在其地建都的王朝和政权也多至10余个。其中有的历史较为短促,甚至不足以具数。最为悠久的当推西汉和唐代。西汉绵延200余载,唐代亦已近乎300年。唐代上承西魏、周、隋,中间并未稍有间断,合而计之,已多超过500年。0002“二十世纪初中国古文献四大发现展”在国家典籍博物馆开展
我要新鲜事2023-05-06 13:20:140001日享一书WJw01《吴国青铜器综合研究》
我要新鲜事2023-06-01 10:57:010000